
五四以后,“婚姻自由”、“恋爱神圣”成为一代知识青年的信条,二十来岁如果不闹出点爱情的风波,仿佛就是对“恋爱神圣”的亵渎。激进一些的,可以同时和几个情人公开交往。比如山西才女吴曙天在1924年时,便同时爱上了叶天底和章衣萍。叶天底是中共早期党员,画家;章衣萍跟鲁迅胡适都过从甚密,也是知名的文人。吴曙天给两个情人写信,“我现在只希望上帝把我这孤苦柔弱的身体,分配得均匀些,分给我的两个情人,你们两人各各管领我的一半罢。”
对,就跟琼瑶剧一样。琼瑶敢这么写,也是一种五四遗风。
然而人终究是没法分成两半的。吴曙天后来跑去北京跟了章衣萍,叶天底挽回无望,便只好发愤革命,把精力全都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去。“四一二”后,叶天底组织“浙东暴动”失败,旋即被捕,杀身成仁。
中共早期党员基本都是五四青年,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这期我们就讲讲中共早期的党内恋爱问题。
1920年共产国际召开二大,会上马林提议,应该为远东的革命者提供条件,让他们可以来俄国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共产国际采纳了马林的建议。21年东方大学建立,同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派留苏生赴俄,此后中共向莫斯科派遣留学生便成为常态。
前期赴俄的都是男人,比如罗亦农、彭述之、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等。东方大学按不同国家分成不同的民族班,其他民族班都有女生,有朝鲜女生、印度女生、波斯女生,但唯独没有中国女生,中国班的三十来个男生颇觉脸上无光。

任弼时(左1)、罗亦农(左2)、张国焘(左4)、刘仁静(左5),1923年摄于莫斯科
而且不仅是面子问题。当时赴俄的革命青年在男女恋爱上都是激进的姿态,互相争夺伴侣的事很常见,别的民族班总会因此闹出不少恋爱纠纷,以致时常要召开“同志法庭”来解决这些爱情官司。中国班的同志们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所以非常压抑,眼光只好对准同性,靠互相调戏来打发寂寞。任弼时当时的外号是“女学生”,王人达被叫做“妇女代表”。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人长的很帅,大概很有做男娘的潜力,王一飞有次在跟外国同志介绍陈乔年时,说他是“中国女人”。
压抑久了就要释放。卜士奇是留苏生中的领袖,22年他回国,刚到北京就向何孟雄的夫人缪伯英发起进攻,在党内闹出了大风潮。后来去上海,又向沈玄庐的儿媳杨之华进攻,让国内同志感觉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都如同色中饿鬼一般。
卜士奇后来脱党,做了国民党的官。
23年时莫斯科东方大学迎来了第一批中国女生,旅莫支部全男班的格局终于打破。这批女生共有五个人,从法国来的蔡畅(蔡和森妹)、郭隆真,还有从国内过去的史静仪(刘仁静发妻)、秦怡君和陈碧兰。其中陈碧兰最漂亮,时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的罗亦农,著名红色恐怖分子李鹤龄和黄平等三人立即向她发起进攻。
罗亦农是支部领袖,有优先择偶权,黄平知难而退,李鹤龄大哭一场。陈碧兰就跟罗亦农好上了,二人开始同居。但陈碧兰在出国前就有男友,是黄日葵,黄日葵是中共北京支部的创始党员,陈碧兰来苏联的路费都是黄日葵出的。留苏同学都鄙视陈碧兰,说她爱的不是人而是地位。
后来莫斯科盛行“倒戈”风潮,倒戈的意思是只要夫妻或情侣一方去苏联学习工作,大概率会移情别恋,就是陈碧兰开的头。

三十年代的陈碧兰
罗亦农长的不帅,外号“罗大嘴”。也许陈碧兰看上的确实不是罗亦农的人,至少在回国前她已经对贫农出身的罗感到厌倦了。罗亦农先回的国,陈碧兰有意避开他,回国后罗亦农在北京工作,陈碧兰在河南,罗去河南找,陈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俩人玩躲猫猫。后来有人给罗亦农出了个主意,让他拿红墨水掺上牛奶假装写血书,罗亦农照办了,但陈碧兰显然并不买账。
陈碧兰后来调到了上海。上海虽然是党中央驻地,但这种爱情“重组”的事情可一点不比莫斯科少。
1924年,张太雷在上海负责团中央的工作。这年冬天他把老婆孩子送回常州老家,自己一个人住在慕尔鸣路的房子里。这地方原来是中央宣传部和《向导》编辑部驻地,瞿秋白本来也住在这里,但此时都搬走了,空出来很多房间,施存统一家就搬了进来。
施存统是中共上海支部的创始党员,当时在上海大学做教授。大教授文质彬彬,教授夫人王一知也知书达礼,还带着活泼可爱的小孩,慕尔鸣路一改过去忙碌凌乱的布尔什维克巢穴作风,逢年过节打麻将,有了生活的气息。

青年施存统
施存统从没想过这会是“羊入虎口”。
施教授大概是很爱老婆的,常用王一知的名字做笔名。但王一知搬进来后,却渐渐地和张太雷谈得投机了,二人时常一起逛街,不久后正式同居。施存统没办法,只能嚎啕大哭。对于这种“恋爱”纠纷,党是要处理的,而一般的处理办法就是把当事人分开。当时张太雷刚当选团中央总书记,很多人拿这事攻击他。党中央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先是决定外派他去外蒙,后来瞿秋白说情,又改派广州。于是张太雷“改组”成功,带着王一知,还有她和施存统的孩子一块南下了。留下施存统一人发疯,直到后来上海大学女学生钟复光给他写信安慰他,施教授才复又光亮起来。
就在张太雷南下广州不久,蔡和森哮喘病发,到北京疗养,留向警予一人在上海。向警予和蔡和森是党内的“模范夫妻”,俩人都是湖南人,向警予是土家族,身材矮小,常年一身内地女学生打扮,非常朴素,和陈碧兰这种漂亮小姐格格不入。

青年向警予
在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前,向警予曾拒绝湘西镇守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的求婚,她只身进入周公馆,斩钉截铁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婚!”1920年6月,向警予与蔡和森在法国蒙达尼结婚,并肩坐捧一本《资本论》拍了结婚照。
向警予很活跃,工运、学运、妇女运动都有她的身影,为党内所称道。另一项被称道的是她的刻板。陈独秀喜欢拿男女关系开玩笑,但只要向警予在场,一定会严正抗议,每每弄得老头子下不来台,其他人就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了。向警予惯于教训人,恨透了党内的浪漫男女,因此她得了一个外号叫“革命祖母”,党内女同志都怕她,杨之华尤其怕,当时瞿秋白已经和杨之华结婚,大概是受到杨的影响,瞿秋白还专门讽刺向警予是“党内的宋学家”。
25年爆发了“五卅运动”,但当时中央宣传上的两员干将却都生了病,先是中宣部部长彭述之二月份就进了医院,完美错过运动;而刚入夏运动进入高潮时,《向导》主编蔡和森又犯了哮喘,就一个人跑去北京西山疗养。中秋节前,彭述之先行病愈,早于蔡和森返回工作岗位。为了庆祝彭述之出院顺便过节,中秋夜党中央的干部们就一起吃了顿好的,饭后还安排了节目,彭述之跳了拿手的高加索舞,向警予起初不肯表演,一群人起哄,只好念了一首李后主词。
也许是舞蹈和诗词起了化学作用,持久的压抑迎来了反弹。当晚曲终人散,向警予便跑到彭述之房间表白。当时很多中央的干部都住在一起,向警予和蔡和森的房间在三楼,彭述之住二楼。“革命祖母”向自己表白,这让彭述之非常惊吓,他便跑到同住二楼的郑超麟那里求援。郑超麟警告他不要乱来,彭表示自己对她没有一点意思,并说向警予也知道不能乱来,这次只是单纯的表白。
到底单纯不单纯,嘴上说是不算数的。这天之后,向警予便经常跑彭述之房间找他“单纯表白”,一表就是两三个钟头。一开始彭述之还来找郑超麟出主意,问怎么办,渐渐地也不来找了。在频繁的攻势下,彭述之发生了严重动摇,没过多久,向警予就表白成功。
于是蔡和森的哮喘终于好了,从北京返回上海。他带了北方特产回来,兴冲冲地准备小别胜新婚,结果向警予却没来接站。向警予本来想瞒他,还和彭述之预订了攻守同盟。但“宋学家”的秉性不允许她这么做,蔡和森一回来她就主动坦白了。
赶得早不如赶的巧。正好赶上中央主席团开会,蔡和森索性就都抖落了出来,要求组织给解决。在坐的一众人,包括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都惊掉了下巴。陈独秀没辙,只好问向警予到底爱谁,结果“祖母”只是伏案一味痛哭,老头子又问她不爱和森了吗?向警予还是不答。清官难断家务事,党中央只好默认维持前状,继续发挥一贯做法,将当事人分开,决定派蔡和森远赴莫斯科去当常驻代表,向警予同去。
向警予当然是不愿意的,她确实已经爱上了彭述之。但开会时她又不肯说,中央决定派她出国,她也没有反对。事已至此,她便只能怪蔡和森自私自利,指责他故意让中央裁决以对自己不利。蔡和森难以自辩,彭述之更是痛苦难耐,两个人一个躺在三楼,一个躺在二楼,什么工作也不干,终日长吁短叹。
这次的爱情风波牵连甚广,造成了重大后果,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党内分裂。蔡和森从此和彭述之结下了深仇,在后来召开的五大上,蔡拼命打击彭。1927年秋天,蔡和森主持北方局,位居时任顺直省委书记的彭述之之上。当时知名的工人党员王荷波被害,蔡和森便向中央打报告,说是彭述之指使人告的密。瞿秋白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正在写文章反对“彭述之主义”,但即便如此,这话在瞿秋白听来也是无稽之谈。
至于蔡和森与向警予,这对“模范夫妻”到了莫斯科也终于散了。李立三和李一纯夫妇是同这对“模范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李立三是好兄弟,为了减轻蔡和森的痛苦,他让李一纯去安慰和森。就在安慰的过程中,蔡和森和李一纯恋爱了。有人说李立三是有意把一纯送走,以便同一纯的妹妹恋爱。事实如何已无人可知,但李立三也和蔡和森结下了仇恨。1928年六大后蔡和森被轰下台,李立三取而代之,就与此有关。向警予后来在莫斯科爱上了一个外蒙人,27年她孤身回国,在武汉还和蔡和森扭打,闹得很难看。后来武汉也开始“分共”,白色恐怖笼罩,向警予坚持工作,直到被捕,在汉口被枪决。三年后,蔡和森死在广州。

25年的风波把“模范夫妻”发配到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彭述之也非常郁闷,每日借酒消愁。然而酒精填补不了女人留下的空洞,只好用另一个女人来填补。恰逢陈碧兰躲罗亦农调到了上海,莫斯科之花漂亮又活泼,彭述之在忧郁中向陈碧兰发起进攻,彭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长,陈碧兰于是和他同居。
彭述之是选派东方大学的第一批中国学生,罗亦农当旅莫支部书记的时候,他当二把手,罗和陈碧兰谈恋爱的情形他恐怕再熟悉不过。而且陈碧兰来上海时还带了罗亦农写的信,信中要彭述之帮忙照顾他的爱人,结果这一照顾就照顾成了彭述之的爱人。
没过多久,罗亦农也调来了上海。他一到上海就去找他的“好同志”彭述之,彭不在家,但陈碧兰却在,罗亦农看见房间里有两张床,还有女性用品,便傻乎乎地问陈碧兰,他的“好同志”是不是找到了爱人。陈碧兰无地自容,好在罗亦农马上就被别的同志拉走了。
事情瞒不住了,只好由瞿秋白出面拉着几个人做调解。瞿秋白大概是为了留一点余地,拐弯抹角地用一个法语词批评陈碧兰,说她是“水性杨花”。轮到罗亦农表态时,他一改写血书的态度,故作轻松,仿佛没什么问题,反倒惹得彭述之说他“冠冕堂皇”。
事情似乎就这么平静了。“没有问题”的罗亦农经常来宣传部玩,“重组”了的彭陈夫妇也常去罗亦农家里,三个人有说有笑。有一次罗亦农跑宣传部汇报工作,彭陈二人还未起床,罗亦农就坐在床边跟他谈事。
是罗亦农大度吗?后来他在党内做大,最后做到中央组织局主任,彭述之要反过来跟他做汇报请示。在蔡和森诬告彭述之时,罗亦农也落井下石,可见这事也并非如他说的那般“没有问题”。
瞿秋白批陈碧兰水性杨花,但陈碧兰此后就一直跟着彭述之。彭述之29年和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党,后来又组织托派,32年被捕,坐了五年的牢。在此期间陈碧兰都没有离开他。解放前夫妇二人逃到香港,后来又辗转各国。彭述之80年代死在美国,陈碧兰陪在身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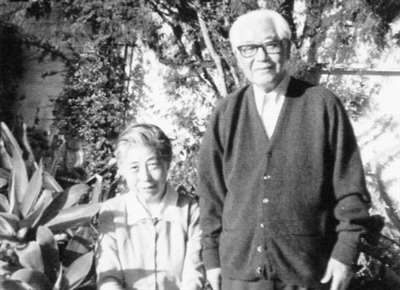
罗亦农失去了陈碧兰,也需新人来填补他的空洞。后来便看上了诸有伦,诸有伦也是有爱人的,她的爱人是贺昌,组织工运的领袖,此时远在莫斯科。于是诸有伦就“倒戈”了,与罗亦农“重组”。此事还惹得施存统抗议,大家还记得施教授吧?施教授就此提出了一条原则,如果女同志要另外爱一个男同志,那必须先同原先的爱人正式脱离关系。
这条原则不知凝结了他多少个不眠之夜。插播一下后续,撬了施存统老婆的张太雷被调到广州,此后就一直在广州工作,八七会议后中共组织广州暴动,他是主要负责人,被打死在广州。王一知转为地下党,后来再婚,一直活到90年代。有意思的是,王一知跑了以后,施存统又和自己学生钟复光结婚,生下儿子施光南。解放后施光南就读北京101中学,时任校长就是王一知。

施存统一家
我们说回来。诸有伦“倒戈”罗亦农,让“原配”贺昌心里有了疙瘩。27年底,罗亦农做了中央组织局主任,贺昌联合几个人向罗发难,推翻了罗亦农在中央的特殊地位。不过此时诸有伦已经再次“倒戈”,和罗亦农分开了。罗亦农后来又去追求独身主义的李哲时,28年元旦二人结婚。四个月后,罗亦农死在上海龙华,李哲时替他收尸。
革命时代的恋爱很有意思,轰轰烈烈而又转瞬即逝。五四影响了一代青年,新文化运动要反礼教,要个性解放,表现出来就是要出走家庭和恋爱自由。这些革命的先驱们互相争夺伴侣,甚至无所顾忌地相互攻击,造成了一幕幕啼笑皆非的悲喜剧。但这也是对人本身价值的肯定,相比于婚姻来说,他们显然更尊重自己的感情,或者说他们压根就不尊重婚姻。
史静仪是刘仁静的发妻,在老家时由父母包办的。刘仁静把她从家里带出来,起初并不喜欢她,就打发去莫斯科读书。史静仪和陈碧兰都是第一批入读东方大学的中国女生。后来史静仪的文化提高了,也就不喜欢刘仁静了,刘仁静倒渐渐喜欢她了。史静仪回国后留在北京工作,爱上了陈乔年,不肯来上海找刘仁静。刘仁静非常痛苦,真割破手指给史静仪写血书,没用红墨水加牛奶的办法。
人人都有表达爱情的权利,无论Ta是否结婚,在这群职业革命家中间是默认的共识。尽管他们自己也能意识到这些恋爱官司里满是浪漫主义的小资情调。
那什么才是“无产阶级之爱”呢?罗亦农抢了贺昌的爱人,贺昌之后又遇到了黄慕兰,黄慕兰本来也有爱人,但刚被捕牺牲。贺昌劝她“决不能有什么‘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于是黄慕兰与贺昌结婚。
1931年,黄慕兰受中央特科领导,负责营救被捕的同志。在营救关向应的过程中与出身上海名门的律师陈志皋结识。出于保密,陈志皋不知黄慕兰已和贺昌结婚,对其一见倾心。中央特科想利用陈家在上海的地位和影响力,便极力促成黄慕兰与陈志皋结婚。至于贺昌,党组织的意见是,“贺昌同志是个很开明的人,他绝不会埋怨你。”
于是,黄慕兰出于工作需要又嫁给了陈志皋。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贺昌留在赣南打游击,第二年被国民党伏击打死。黄慕兰一直活到2017年。

黄慕兰
革命家是随时会掉脑袋的职业,因此“无产阶级之爱”不仅是革命事业至上的大爱,也很容易因为兵荒马乱而被还原为单纯的生理活动。陈乔年在东方大学读书时就受到了“杯水主义”的影响,他说,“革命家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只有性交,因为革命家的生活是流动性的,因而不能结婚;同时革命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种小布尔乔亚恋爱的玩意,所以没有恋爱。走到哪里,工作在哪里,有性的需要时,就在哪里解决,同喝一杯水和抽一枝香烟一样。”
他哥陈延年显然也很赞同他,陈延年甚至更进一步,他从不搞男女关系,从来没有爱人,除了一心扑在革命上,唯一的爱好是吃。后来陈乔年自食其言,跟史静仪谈起了恋爱,也闹出了不小的风波,陈延年便很罕见地对弟弟流露出不满。陈延年1927年死于上海龙华枫林桥畔,第二年,陈乔年也在这里就义。史静仪后来再婚,刘仁静跑去组织托派,被开除出党,二人都活到了解放后。
王一飞是继罗亦农和彭述之之后的又一任旅莫支部书记,陈碧兰刚调到上海时,王一飞是她的领导。王一飞为了解决性的需要,与一名叫张亮的工人党员同居,二人之间没有感情,纯肉体关系。陈碧兰还夸他实现了“无产阶级化”。后来因为生活习惯不合,王一飞与张亮很快分手了,张亮后来又嫁给了项英。
王一飞2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死在长沙。张亮后来牵涉瞿秋白牺牲一案,在延安被处决。

除了杯水主义之外,随时会牺牲的预期还导致同志之间的爱情蒙上了一层淡漠。颜昌颐是最早筹建中央军委的党员之一,他本来与夏之栩相恋多年,为了工作两人分别在京沪两地,后来夏之栩便和赵世炎恋爱了。有一次颜昌颐和赵世炎同桌吃饭,有人问起颜昌颐他爱人的近况,颜昌颐大方表示夏之栩现在是赵世炎的爱人,语气十分自然,想必分手也十分顺畅,反倒给赵世炎闹了个大红脸。
1929年,因叛徒告密,颜昌颐枪决于上海龙华。而早在两年前,赵世炎就被捕牺牲了。
革命是暴烈的活动,但革命也是浪漫的活动。这不是小资情调的小浪漫,而是一种层次更高的大浪漫。从这个意义上讲,恋爱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私事,恋爱同样也能反映一个人根本上的革命态度。革命、革命,革到最后一定会触及人的亲密关系,中共最早的革命先驱,正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又被动荡不安的国民革命磨砺后,才最终将生死置之度外,演绎出如此细腻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爱情与人生。
当然,现在的人肯定会觉得狗血,一定还会有人指责我丑化革命先烈。我声明一下,这些事情都有据可查,全部出自当时人的传记或者回忆录,比如《郑超麟回忆录》《黄慕兰自传》,还有陈碧兰和彭述之的回忆录,等等,各位大可放心去查。
现在喜欢神化革命先驱,喜欢为尊者讳,这也说明革命早已走向了其自身的反面。革命先烈们的生平是要经过审查的,在官方的叙事中,他们早已被抽干了饮食男女的活力,被高高供起,成了本朝太庙里的神像。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脱离群众呢?
神像是用来拜的,是用来隔离生活的,革命因此变成一个远在天边的符号,曾经的革命因此和当下的现实发生断裂,鲜明的红色因此被漂白了,最终成了粉红色的养料,滋养了当今的保守现实。
有些跑题了。谈先驱们的恋爱史,一方面是要还原他们作为人的属性,二来也是为了和当前发生联系,最后都是要让现在的人能真切地感受这些革命者曾经的鲜活,和他们所处的时代脉搏。
革命先驱们所追求的理想不仅是每个人都过上温饱或者物质富足的生活——这不过是牛马的理想,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没有压迫,人人自由,能充分表达与发展自我的社会,而这样的理想,恰恰不是那些被高高供起的神像所能承担的。
因此将他们还原为人尤其必要。只有把他们从神坛上请下来,我们才能发现,原来革命者与我们并无不同,原来我们也可以是革命者。

END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