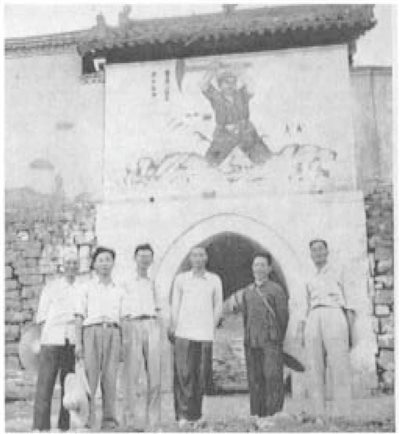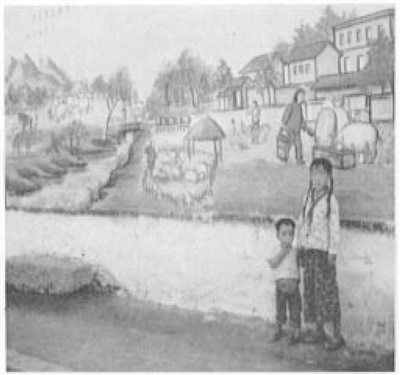作者:伊莎白(Isabel)、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
翻译:放野
校对:鸡卵是青蛙
激流按:2023年8月20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人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学拓荒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专家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女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8岁。
为纪念伊莎白·柯鲁克,我们从8月21日开始,连载伊莎白·柯鲁克与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合著的《阳邑公社的头几年》(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1947年,伊莎白、大卫夫妇为考察和报道中国解放区土改运动,穿越重重封锁来到河北涉县,亲眼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为此深深震撼,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部名著。
新中国成立后,伊莎白、大卫夫妇尽管在北京有了新工作,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十里店成了阳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1959年和1960年的夏天,他们又回到了十里店。《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主要是根据这两次访问期间所收集的材料编写而成。本书于1966年由伦敦的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出版,目前尚无中译版。本书详细描述了阳邑公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组织,包括农业生产、妇女就业、扫盲运动、青年组织、政治和军事组织等,值得一读。
九月成立的阳邑公社,一开始只是意味着用一个公社委员会取代十个乡镇和三十三个合作社。这四十多个单位的实际合并是后来的事。与此同时,成立了一个公社党委来指导发展。任清美和郭恒德在继续担任本村领导的同时,都成为公社的副主任和党委成员。
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不仅涉及规模和组织问题,且涉及所有权和分配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理论指导。这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8年8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可以找到。然而,这个决议虽然总结了中国各地农业合作社争取建立更大社会组织的经验,但也只提供了广泛性的指导,因此也为地方的主动性和试验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关于规模,该决议建议公社应以统一的乡镇单位为基础,并应包括约2000个家庭。然而,这样的安排允许有相当大的差异。在一些地方,如果符合地形条件和生产需要,几个乡镇可以合并成一个由6000或7000户组成的公社。在阳邑,甚于突破了这个规模,十个乡镇和另外两个乡镇的部分地区被合并,总共有10,000户,这就把洺河上游所有地形崎岖不平且贫穷的合作社和河谷宽阔地带一些更富裕的合作社结合起来。决议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决议指出,虽然不鼓励建立1万甚至2万户的公社,但也不必反对。[1]
1.在银海区中心的一个小丘上挖出的生活区,尽头是写着大跃进口号的塔楼。
2.乡村壁画展示了前进中的农民劈开道路上的大山。壁画前站着的是县政府的干部。(县长王德恒身穿深色制服)
3.乡村壁画宣传饲养牲畜的好处。
4.阳邑县城墙上的壁画。口号是:“乘胜前进,提前和超额完成全年的任务”。
最初提倡的程序是“改上不改下”。因此,新成立的阳邑公社委员会将现有的乡镇委员会改组为公社工贸部、文教部、保卫部。
同时,合作社像以前一样继续耕作——但以“生产大队”的新名称进行。
新成立的公社委员会、党委和各部门的任务是将重组工作落实到这些大队及其工作小组;这样做不仅能避免生产中断,还能刺激生产,领导水利兴修和炼钢运动也被包括其中。
谈到这一时期,公社党委委员之一金汉成说:“我们很难跟上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在秋收和耕作之余,我们还面临着这么多新的任务。”
然而,合并的工作还是进行了,新公社的领导层一方面紧盯八月决议,另一方面时刻注意可能出现的问题或错误。
至于所有权,决议只是警告说,所有权应该继续由集体所有,而不应该转为由全体人民所有。但这种集体所有制的确切性质并没有明确规定。在阳邑,公社成为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意味着,除其它事项以外,公社还接管了资金和重要的农用设备。这样一来,三个山谷下方的大队拥有的三台拖拉机现在成了公社的财产,因此属于所有33个大队。这三台拖拉机是新成立的公社拖拉机站的核心,位于阳邑镇郊区。小冶陶的发电厂也成为公社财产,其电源线也延伸到公社中心。
公社还拥有驴车和骡车、犁、耙和其它大型工具(不包括锄头、镐和手工工具)的所有权。这通常不涉及将它们从大队中移出,但随着所有权的转移,公社委员会能够而且确实重新分配了一些牲畜和工具,主要是从较好的大队中分配给需要它们的其他大队。同时,山里各大队的一些羊群也被分配给山谷里的大队,让他们开始从事畜牧业。
总的来说,改革似乎进行得很顺利。然而,某些问题也引起了公社委员会和党委的注意。
赵庄(这个村庄的菜园子都很不错)的金书记说,当他们听说要把所有的资金都交给公社的时候,赵庄的干部们跑出来买了三辆自行车。当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大队。赵庄是一个很大且繁荣的合作社,已经攒够了买自行车的钱。干部们意识到,公社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为所有大队提供这样的东西。
另一个最繁荣的大队——阳邑大队的做法有所不同,但动机相似。在社会主义合作社时期,社员们把他们的马车和牲口集中起来,从而使合作社能够从事短途运输这一有利可图的副业。这些物资的原主人将在五年内从收益中得到回报。在安排向公社转移资金和农具时,阳邑大队干部提前三年将钱全额偿还给这些车和牲口的原主人。
诸如此类的行动耗尽了公社的资本。
另一件事也让公社领导层忧虑。在赵庄和十里店村之间的石洞,一辆驴车和两把犁被丢在田里腐烂生锈。既然它们是公社的财产,大队便不再对它们负责,因此也不会处理了。
决议大部分事项都涉及劳动报酬和所有权问题。因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即以“按劳分配”原则为基础。决议建议,没有必要急于改变原来的报酬制度;需要的是避免对生产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具体的报酬制度应根据具体条件来确定。决议指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向工资制度转变。但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按工作日支付的制度。”
在阳邑,人们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不仅可以转为工分制,而且可以转为工分加免费粮食制。1958年,粮食亩产达到每亩313斤,这意味着平均每人约630斤。这些数字是史无前例的,农民们为自己贡献了免费的粮食。他们称之为“铁饭碗”,而不是以前的“破饭碗”,在土地改革之前,当农民失去生活来源的时候,就用这个词“破饭碗”。这种用词的变化比决议中的所有号召都要有说服力。
免费提供食物的想法并不是突然产生的。在土地改革之前,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挨饿。每年,农民们都以树皮、糠和野生植物的根为食,以熬过“青黄不接”的时间。每年村子里都有人饿死。在一些地区,在平均每两年发生一次洪灾或旱灾的年代里,人们纷纷逃难,许多人再未活着回家。1936年、1942年和1943年,水灾和旱灾频繁发生,灾情严重,波及面广,一年之内就有数百万人丧生。路上到处是尸体。因此,温暖的家和衣服、减轻劳动负担的机器、休闲活动,这些都是广大中国农民做梦都不敢想的。他们真正梦想的是拥有一块土地,在那里可以种植足够的粮食吃饱饭。
土地改革实现了这个梦想。它与党领导的其它改革一同赶走了饥荒。但它并没有带来富足。改革使农民得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但却无法全年吃饱。直到合作社成立之时,不从事最繁重体力劳动的妇女在一年中部分时间里会用谷糠充饥——甚至富农家庭的妇女在土改前也是如此。较好的粮食留给了男人,他们在田间的繁重劳作要消耗更多能量,但即使这些男人也没有足够的食物。中国农民的日常经验中没有“饱腹”一说。截至1957年,中国有30%的农村人口要靠政府或村里的救济才渡过难关。[2] 1958年的收成是土地改革前最高收成年份的两倍——2.5亿吨的粮食。[3]随着这次丰收,公社的成立和对合作社分配制度的改革也随之而来。公社和分配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国的各个地区都出现了免费食物。
除了免费食物之外,阳邑还在工资制度中引入了中央委员会决议中没有提出的另一项创新举措,即将工资直接支付给劳动者本人,而不是支付给户主,因为在互助组和合作社中,一个家庭所有成员的工资都交给户主了。父权制家庭制度的这一残余现在受到了最后一击。
工资标准和免费食物的发放是在考虑到整个公社的基础上制定的,只是根据劳动者的类别而有所不同。然而,这些类别本身并不因大队而异;现在唯一保留的工作记录是缺勤记录,缺勤日的工资会从当月工资中扣除。劳动者个人完成工作的实际数量和质量不再被考虑在内。
随着工资制度的彻底变革,各种问题也暴露出来了。
公社领导很早就注意到,在阳邑大队,工作节奏正在放缓。大队里已经开始传出消息:那些在列章山上的人们过得很轻松。他们认为,现在他们和我们以及其他山沟里的大队在一起,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也不需要那么节俭了。公社党委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在偏远的列章,每个人都在为公社唱赞歌,但也有不少人不像以前那样顽强地在石山土里刨食。列章大队党支部书记自己也满意地说:“我们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把合作社合并成公社。我们这里每人只有一亩多的石子地。现在我们可以从山谷里的大队那里得到帮助了。”
穷队和富队之间的矛盾
新的公社领导层尽管“很难跟上事态的发展”,但还是了解了合并后的各种问题,并对其进行了仔细研究。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所追求的是解决“主要矛盾”。
党委金书记说:“最后,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公社的主要矛盾是穷队和富队之间的矛盾。经济条件好的大队——拥有最多、最好的土地的大队——在办合作社时收入最高。现在他们认为,作为公社中的一个大队,他们的收入会下降到比较穷的大队的水平。另一方面,较穷的大队认为,只要与较富裕的大队联合,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高枕无忧。”
总之,与总路线的精神相反,一些较好的和较差的大队都没有全力以赴,生产正在放缓。而解决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巩固公社的关键。
因此,公社党委发起了一场教育运动,以说服较贫穷和较富裕的大队,公社对他们都是有利的,而且双方都应该全力以赴,为公社和自己的利益服务。
党委指出,在土地改革以来的每一次进步中,经营单位越大,亩产就越高。[4]因此,他们推断,对于比社会主义合作社大三十倍的公社来说,这种趋势将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党委认为1959年的计划完全有可能实现。该计划要求亩产比1958年公社空前大丰收时的平均亩产还要提高20%。这比那些较富裕的大队取得的成绩还要高。甚至这个数字被认为是绝对可以保证的最低目标。看来完全有可能达到的实际目标是每亩400斤。
对于大山深处的穷乡僻壤,会议则强调了另一个问题,即公社可以使农业更加多样化,使土地的使用更加合理。小冶陶大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该大队虽然在山区,却是公社中最富裕的大队之一。这些事实被用来消除依赖较富裕大队的想法,并加强自力更生的精神。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较贫穷的大队引入了两个新的制度:“保工保产”和“评工评级”。这意味着在每个工作小组中,规范的制定要以工人们各自的技能、体力和以往的表现为主要根据。
这就是领导层的措施——教育和组织措施,以抵消任何可能阻碍新生公社发展的趋势。
政治和行政结构
公社现在已经成形了。阳邑人民有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包括工业、农业、贸易、教育、军事和福利服务。这个新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单位将“管理”(将会继续得到发展和完善)和“国家权力”(最终将“消亡”)结合在一起。
最高管理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每两年由16岁以上的全体公社成员选举产生,如果需要,每年举行两次或更多次会议(这是选举县人大代表的机构,因此间接选举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次公社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根据公社的实际情况,决定贯彻党和政府政策的必要措施。这涉及生产和分配的总体经济计划,制定社员的福利计划等。公社代表会议还负责听取公社各部门和各阶层成员的意见。代表们应提出选民的意见。代表大会的第三项职责是监督公社委员会,即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负责代表大会工作的机构。在会议期间,代表大会要检查和监督其决定是否得到执行,以及干部中是否存在腐败或不称职的情况。
公社委员会由大会选出的31名成员组成,对大会负责,下设四个部门、一个办公室和一个技术站,有 20名专职工作人员。这些部门是保卫部(相当于警察局);军事部(负责民兵和征兵);工贸部;文教部。
每个部门都在公社的分区设有分支机构,被称为 “管理区”[5] ,共有25名全职工作人员。这些分区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公社绵延近30英里,干部们出行主要靠步行,偶尔骑自行车。
这就是公社的行政结构。在评估所带来的变化时,一位公社党委书记说:“公社组织有利于集中领导,节约干部,也有利于统一规划和行动。它为成员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并有助于促进生产。”
该地区未被并入新单位的仅有的几个重要组织是党的地方支部、共青团和妇女联合会。[6]
初获成就
在进行合并的同时,公社领导还推动了水利建设和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同时,公社还注重田间管理,以确保尽可能多的收获秋季作物和耕种冬小麦。
就在公社成立的那个月,公社对困扰人们许久的“敌人”——旱灾发起了“攻击”。共和国渠增加了一条五英里长的分支,在那之前,渠道只是将水从小冶陶带到阳邑。新的延伸部分将水带到十里店村,在那里挖了一个很深的石砌池塘来蓄水。挖掘花了2800个工作日,所经过的土地不久前还属于不同的合作社。现在,这些合作社不再沿旧渠道派人看守,而是出力修建新渠道。
水渠和池塘竣工后,村里举行了庆祝活动,这使得灌溉面积达到了 100 英亩——占十里店所有农田的七分之一。当然,同时也解决了村里一直存在的饮用水问题。现在,即使是最疼爱女儿的母亲也不害怕把女儿嫁到十里店村。
公社成立不到五十天,就生产出了3000吨铁和750吨低级钢,这些产品适用于制造农具。尽管产量和质量有限,但这足以为当地工业化奠定基础。公社农具制造和修理厂的建立及其柴油发动机、蒸汽泵和车床,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同时,公社还开展了一项运动,使肩上的担子卸下来,装上轮子,并改进轮式运输,为老式的吱吱作响的木轮车装上滚珠轴承和橡胶轮胎。很快就有67辆骡车配备了这种装置。
这些成就加上农业大跃进,使社员的收入大增。这反映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消费品销售的急剧增长上。这一时期(1959年上半年)的销售额是1958年上半年的三倍,而1958年上半年正是农业大跃进和公社成立之前。
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商品上,也体现在服务上。社区食堂,以及在柏林等社会地位较高的村庄设立的托儿所、幼儿园、裁缝店和妇幼保健院,都是为了把妇女从厨房和院子里解放出来,在社会服务和经济单位以及田间地头从事有偿工作。对这些妇女来说,工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新奇的是在集体中而不是在家里工作,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们可以亲手领取报酬。即使对那些以前在田间工作的妇女来说,这也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
这些都是阳邑公社成立几个月以来获得的成就。
注释:
[1] 事实上,这样的规模被证明过于庞大,在1960-1961年的冬天,阳邑公社分成了四个,从而使规模更接近决议所倡导的规模。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趋势。到1962年底,公社的数量已经从26000个增加到70000多个。见廖鲁言,《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北京评论》第44期,1963年11月。
[2] 李清泉,《人民公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辉煌的十年》,外文出版社,北京,1960。
[3] 中央委员会给出的经过核实的数字纠正了先前的夸大估计。见《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外文出版社,1959年8月,北京。
[4] 见24页表格。
[5] 管理区,以下称“区”。
[6]见第三部分。
相关文章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