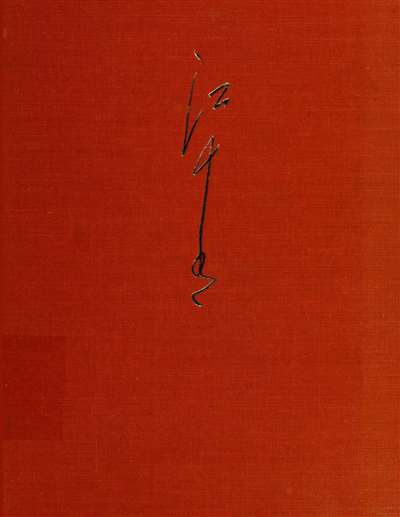
(接上)前情介绍:李进同志(二)
2、梦回红楼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皆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18世纪的中国古典小说,但鲜有西方人知道这部小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读过它五遍、十遍甚至二十遍,对它的解读既是一种文学爱好,也是一种思想成熟的过程。江青对《红楼梦》的评论展示了她对小说的掌握,也预示着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密切参与了对文学和艺术的颠覆性的评估。
其他朝代的缔造者可能会选择“焚书坑儒”,彻底摒弃一部如此生动描绘令人不快过去的小说。而共产党领导人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与其共处,并以关键方式将其纳入自身掌控。其原因可从政治策略中找到。例如,对一部深深扎根于旧传统的小说进行重新解读,比起彻底删改,更不具破坏性,也较不易激起民众的抗议。巧合的是,这部小说本身就具有自我纠错的特质:其梦幻般的叙事透露出对所描绘社会制度的怀疑、幻灭与否定。此外,毛主席和党对自己的教育能力充满信心——他们相信,人民可以被教导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早期解释,并至少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阅读或公开讨论该小说。
为了理解江青对《红楼梦》的评价,简要概述小说情节并梳理主要人物,对西方读者尤为有益。书中所有人物均与贾氏家族的两大分支相关联,一支居于宁国府,另一支居于荣国府。
荣国府由贾赦领导,他是家族太夫人的儿子;宁国府名义上由贾珍主持,他因父亲出家而继承此位。贾珍的侄子、太夫人的另一名儿子贾诚,则附属于荣国府。王熙凤早年嫁于荣国府贾赦长子贾琏——一位能干且有影响力的女性,但她在小说进程中病逝,其行为被揭示为最终导致贾府被宫廷官兵抄没的原因。
贾政与妻子王夫人的儿子就是宝玉——故事的主角。宝玉原本应努力学习,准备科举以成为高官。然而,宝玉多情而感性,更喜与表妹和侍女为伴。他从小玩伴并心仪的表妹是林黛玉——太夫人的神秘、神经质孙女。另一位美丽的表妹是薛宝钗,她搬入荣国府,本应成为宝玉的妻子。婚礼之夜,林黛玉因心碎而去世,但宝玉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这桩婚姻并未给宝钗带来幸福。最终,宝玉考取功名,却很快遁世出家,留下宝钗与一名孩子。
如此简略的梗概不可避免地强调了爱情元素,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小说人物众多,个性鲜明,长期以来吸引读者,因为它展示了消逝贵族私生活的辉煌与腐败。十八世纪的这些富贵闲人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人倡导的朴素农民风格所力图摒弃的一切社会、文化与政治诱惑:宗教神话与象征、豪宅与奢华生活、对穷人的片面关注、官场中的勇敢与腐败、豪门家族借机膨胀以牺牲国家利益、以及公然的情欲行为与性偏差。
超越社会全景的描绘,这部小说巧妙地运用了形而上的对比手法:外在的辉煌与内在的衰败、感官享受与苦难、虚构与现实、现实与幻象、醒世与梦境。精心铺陈的比喻将这些对立的领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一)
“《红楼梦》我读过五遍,”毛主席在1964年说,“但我没有被它影响,因为我把它当作历史来看待。”在朗诵了许多关于仙女、玉石和宫殿的长篇段落之后,江青提醒我:“不要把这本小说当作单纯的故事来读,而要把它当作展示阶级斗争的历史书来读。”
正如她在历史题材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中所体现的,江青将自己呈现为第一位向领导和全国揭示《红楼梦》文学批评中不公正之处的人。然而,她花费几个小时与我讨论这部涵盖故事、诗歌、神话与历史的作品,并非完全出于审查动机。在她的叙述中,她的双重人格再次清晰展现:在公共职责上,她是警示主人的文学守望者;在私人层面,她是热情洋溢的故事爱好者。
江青轻松地承担起阐释小说作者身份与意义的问题,这是复杂且需要真正专业知识的课题。尽管她引用的部分细节和对小说政治问题的判断,或因过度热情或疲劳而存在偏差,但她显然掌握了新批评的核心思想,也无疑是这些观点的源头。她长达数小时的独白中表达的几种解读,后来在一年内成为官方出版的指导意见的一部分。
围绕这部小说的传奇始于其创作之谜及最终定型的猜测:作者是单一还是多人?现存手稿的真实性如何?小说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历史环境与人物?这些问题可能会被无休止地讨论,也许永远无法得到最终答案。
前八十回的作者通常被认为是曹雪芹(约1715–1763),他出身于一个富裕且有影响力的家族,家族在康熙年间经营南京的皇家织锦厂。康熙将清朝带至鼎盛,又逐渐走向衰落。同样,曹家也失去了财富和皇室宠信。小说中的贾家则对应现实中的曹家。小说开篇前,贾家已被皇帝封授两座公爵爵位;在故事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女儿成为皇妃,与宫廷紧密联系;而在后续情节中,家族的荣华逐渐衰退。
(二)
由于江青一开始并不读外文,所以她接触的外国文学有限。但从她读过的译本来看,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十八、十九世纪的书籍在对人际关系的细致分析上能与《红楼梦》相媲美。
在外国作家中,她尤其钦佩马克·吐温,他是一位“进步人士”,刻意揭露了社会的不公平。即便如此,她继续说道,他笔下的主要人物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努力向上爬。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男主人公也是如此。司汤达《红与黑》中的男主人公于连也是如此,他渴望获得军官职位;他的岳父想为他买一个爵位,并送给他一块手表和其他资产阶级的象征。尽管这种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主题令人厌恶,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对司汤达的钦佩。
《红与黑》是一部“不朽的”作品,它将永远在世界文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它反映了19世纪初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它不仅描述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也描述了教会与国家机构内部的争斗。某些法国修正主义批评家与旧时代的《红楼梦》批评家一样,将《红与黑》主要视为一个爱情故事,从而降低了它的历史意义。至于司汤达,他实际上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他出生并成长在一个小镇,最终为了“王朝”服务而走遍了欧洲。然而,他生活的这一方面却提升了这本书作为当代政治舞台的镜子的价值。
她长期以来仰慕的另一部伟大小说是《金瓶梅》。这部作品创作于明朝,故事背景设定在山东的一个小镇,与她儿时熟悉的商业中心并无太大区别。书中对性关系的描写如此露骨,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人都无法阅读未删节的原版。她一本正经地表示,尽管有传统习俗,但她拒绝阅读删节版。她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文学篡改。
江青称:“我对《红楼梦》算是半个专家。”她首次阅读此书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目的是发现其中的政治真理。围绕该书的持续争论背景值得回顾,因为它凸显了一些领导人多年来不得不应对的顽固人物。1954年,她在家休养时,随手翻阅一些期刊,偶然注意到山东大学《文史哲》9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李锡凡与蓝凌,两位显然才华横溢、当时无人知晓的学生,对俞平伯教授近期的评论提出批评。俞平伯的学术生涯建立在对该小说公认的“资产阶级”欣赏之上。江青立刻将文章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该文有价值,应广泛传播。他请她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李锡凡的文章(江青在讨论中始终强调李锡凡而非蓝凌),编辑们照办了。
与此同时,江青开始了自己的调查。她了解到,李锡凡最初将文章投稿给《文学公报》(上海出版的主要文学期刊,由胡风、丁玲等人主编),却被拒稿。随后他将文章投给《人民日报》,同样遭到拒绝。直到江青以毛主席的名义向编辑们提出要求,他们才同意转载。之所以《人民日报》最初拒绝刊登,是因为某些显赫人物的权势以及他们仍然崇尚的文学学说。江青指出,“毫不意外”,俞平伯与胡适属于同一派系。李锡凡的文章正中二人的“要害”——即资产阶级政治的文学表达。然而,这两人在1920年代建立的权威至今仍极为广泛,若非江青亲自干预,李的文章所代表的新学术思想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传播。
江青当时仍在康复期间,她特意前往《人民日报》北京办公室推动李锡凡的文章出版。接着,她出席了中央宣传部的会议,将文章交给负责的周扬和胡乔木。他们翻阅后带着轻蔑的讽刺评论道:“这都是小人物写的。小人物怎敢批评另一个小人物——俞平伯?”江青勃然大怒,但当时没有透露《人民日报》已同意刊登此文。
在她的推动下,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向政治局及其他政府部门发出公报,题为《〈红楼梦〉研究问题》,并召开会议审议此事的各方面问题。江青记得清楚,毛主席在会上理论性地谈到了“大资产阶级对小人物的压迫”以及“新兴人物遭受资产阶级压迫”的错误。关于小说的意义不难理解。尽管俞平伯和胡适属于理想主义“资产阶级压迫者”的同一派系,宣传部和文化部的领导——周扬与陆定一——长期欣赏胡适与俞平伯合作研究《红楼梦》的成果。此时若完全否定他们,会让现任领导失面子。
1920年代,胡适与俞平伯研究这部小说时,“垄断”了珍稀的十六回本和八十回本,导致“群众无法接触到它们”。但到江青介入时,这两种珍本的原件已由公共机构保存,其他版本均为影印本。八十回本的原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江青曾借阅过一次,并要求复印一份。当一些“资产阶级权威”发现她的请求时,立即对她提出指责。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希望为自己的目的独占这些原件。
后来的评论价值参差不齐。江青说,有一位当代评论家周汝昌写过一本书,题为《红楼梦新证》。虽然他的观点接近胡适一派,但唯一的优势是他利用了清朝宫廷档案。尽管他的考证方法存在缺陷,这本书仍值得阅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周汝昌遭到批斗时,江青曾试图保护他(她迅速补充道,这件事直到现在她从未向任何人承认过)。
江青指出,虽然《红楼梦》以小说形式写成,但其生动程度堪比历史。小说描绘的社会全景几乎百科全书式。书中三到四百个人物中,作者选择重点描写约二十人的生活。他关注的二十人是“主人”,其余人物则是“奴仆”,靠主人府邸产生的垃圾为生。
八十回本的独特价值在于包含了作者曹雪芹的大量批注。这些对小说的二次思考在历史上极为重要。由于曹雪芹从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视角写作,他的判断当然带有反动色彩,但现代读者必须意识到,他的思想在当时实际上相当进步。
她继续说,所有文学作品都必须结合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来讨论。曹雪芹在二十多岁时创作《红楼梦》,并在十年间不断修改。通过研读各版本的批注,她像前人一样认定,曹雪芹曾准备写作续篇或下半部。由于他去世时没有子嗣继承作品,续篇落入一些自称“借用”但从未归还的人手中,因此原作遗失。曹雪芹的笔记显示,续篇的发展是悲剧性的:家族失去官运宠信,财产被没收,曾经生活富丽堂皇的人沦为乞丐。
原续篇失落后,其他作者自行创作续篇。如今完整的一百二十回本的最后四十回归功于高鹗,但他没有署名(让人误以为是曹雪芹的原作)。在这一部分,宝玉通过了乡试(称为“举人”),离开家和孩子,出家为僧。
江青指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角度看,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并非为了改变社会,而只是试图修补社会的弊端。当然,他对官僚体制不满,但绝不会去主张推翻支持该体制的王朝。他只是试图修补当时社会的“裂痕”。即使有这样的局限,《红楼梦》还是唱响了封建贵族的挽歌,套用曹雪芹的话来说就是:「满纸荒唐言。」
待续……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