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资本论》:新古典主义批判(上)
愿君多采撷
——题引
【阅读提示】此为《保卫资本论》(2017修订版)第九章,——首版(2014)该章附有一个副标题“康德主义路线之一·立的基础”。肇因康德主义,现有经济学始终陷于体系之分裂,其状况可谓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大体说来,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原理可用6句话概括:无“母”无“体”;皆“子”皆“用”;以“母”设假;以“子”设用;以“子”假设;以“用”结论。前两句是三段论推理之大前提,中间两句是三段论推理之小前提,后两句则是三段论推理的结论。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文《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与方法论命题——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及其创造性转化》,《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然则与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基础势必包括本土化规定之学术研究,尤其本体论批判路径的原创研究,其理论构造乃是着眼于方法论建设之要求,亦必然引出中华典籍经典性与当下性之探究问题,从而涉及有关国学马克思主义之“深思”。可喜的是,时代驱行,时轮回转,2018年以降悄然开启的“抗美”时代是再造了历史上的“中西关系状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文化架构彻底击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其整体预示了中国经济学建构之文明基础和理论基础,我们需要于其中寻觅本真的方法论机理(亦可进一步参阅拙文《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2期)。
(本文转自《保卫<资本论>》修订版P214-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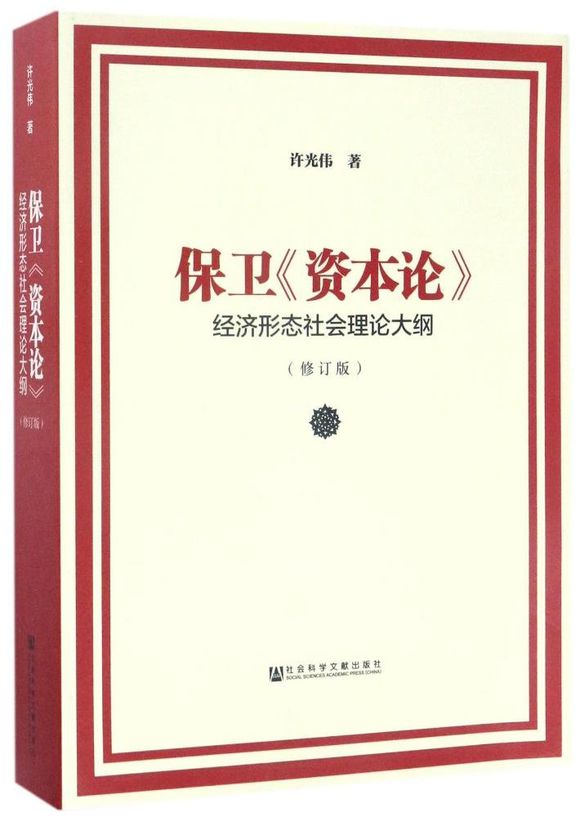
楔子
(一)
康德的“自在之物”既然根本不同于“我们的”经验对象,于是经验论者(实证主义者)就认定它仅仅是一种“本体论的承诺”,是纯粹的假设。但康德本人并不认为它仅仅是假设,而肯定它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在经验之物之外的存在。卢卡奇认为,这一点,既表现了康德哲学的矛盾,也表现了康德哲学的伟大和深刻之处。康德赋予“自在之物”这一概念的含义,是说它完全超越了人们可理解性的范围而成为不可捉摸的既定性的存在。这种“存在”是确实存在着的,人们也切实地感受到了它的作用和影响,但由于它是超验的、既定的、给予的,对人的认识理性来说是完全异质的、异在的,人的理性不曾参与它的生成,故而对它的历史起源和内在本质也就无从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结构从物化意识的立场来看俨然就是康德的“自在之物”。对于这种“自在之物”(物化结构),资产阶级的有限的理性(认识能力)只能认识和把握它的现象,而不能认识和把握它的总体和本质。根据卢卡奇的理解,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学说,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在哲学上的反映。康德哲学的历史功绩就是他最终发现并深刻地阐发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二元对立和内在矛盾。(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
(二)
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三)
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八版)
(四)
克思的挑战,特别是在获得了越来越具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之后,使得资本主义陷入防守地位。但马克思学说有一个理论上的弱点,即它的奠基性的价值理论。不久,在欧洲和美洲,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英格兰的杰文斯、瑞士的瓦尔拉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以及美国的约翰·贝茨·克拉克都声称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古典的”分析让位于“边际主义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了。(D.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
(五)
19世纪以降,面对自然科学心生畏怯的经济学家就一直致力于模仿物理学来构筑自己的学科(“均衡”概念是“卑躬屈膝地”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表现)……奥地利学派家则一直以来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继续试图将经济学化约为有关人类事务的牛顿力学的努力。(G·B·麦迪逊:《现象学与经济学》)
(六)
在正统经济学内部占优势的当然是新古典学派。1870年后,正是该学派横扫了资产阶级的知识界,并大声宣称自己是“科学的”“客观的”,从而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的。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急于使自己的“科学”脱离已沾染前古典学派的社会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些新古典的经济学者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必须实施在物理学中所发现的同样的科学论证标准。他们认为这首先意味着经济学应该离开历史的特殊性去探寻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和范畴。他们试图找到一种系统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用于所有的经济制度、所有形式的人类社会、所有的历史进程。因此,他们脱离历史本身的抽象切断了与政治和对特定社会制度的研究之间的联系。这样,为了成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就必须是超历史的、超社会的和超政治的。(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
(七)
与所有的科学(包括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经济学也包含着一种隐含的哲学,也即对于什么构成“实在”(在近代,占据主流的笛卡尔主义的看法是,“实在”从根本上就是运动着的事务)的看法,及与此相关的对于人的理解(它的对象是“实在”……近代人普遍地将“心智”视为自然的简单“镜像”)之性质与功能看法。这种哲学通常只作为隐含的前提,并且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不过,它确实渗透到哪怕是最具有“经验”色彩的科学研究中,而如果这种哲学并不适合于某些学科的研究对象领域,那么就经常会导致不幸的后果。现象学家认为,这种哲学经常诉诸实证主义——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经常如此,而它却完全不适合于研究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即存在着的人的经济活动。(G·B·麦迪逊:《现象学与经济学》)
(八)
虽然操作主义对经济学的影响不如它对心理学的影响大,但是似乎萨缪尔森也将操作主义来了个颠倒。这——就像穆勒的李嘉图经验主义的张力,凯恩斯极力驳斥对李嘉图经济学的批评,凯恩斯的马歇尔主义,罗宾斯著作中的政治经济学与方法论的联系,奥地利学派和哈奇森,以及弗里德曼努力悬置假设——开始质疑仅仅是从科学哲学的货架上提取(相对原始的)观念的方法论观点。似乎政治、环境和偶然深深根植于选择过程之中……(从中看出)哲学依然是方法论发展的源泉。(D·W·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
(九)
东西方的空想资本主义经济学,都不愿意承认古典经济学的起点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供求均衡的微观经济学。(陈平:《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评皮克迪新书<21世纪的资本>》)
研究对象的“改造”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是边际革命以前的经济学。1870年以后出现的边际选择理论、有效资源分配理论以及帕累托最优状态理论,都没能渗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当罗宾斯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在相互竞争的用途之间分配稀缺性资源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是在胡说八道。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对价格的经济职能(有别于会计职能)不感兴趣,对相对价格作为稀缺性指标的意义也不感兴趣。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微观经济学。”【注: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65-66页】
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来,情况的确如此,甚至远比想象的要更为厉害的多。“事实——价值分离被用了进来,经济学家们宣称他们自己(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置身于道德问题之外。因而,对资本主义的辩护问题就留给哲学家、政治家和作为公民的经济学家去做。当然,经济学的结论仍然是重要的: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有效率,或者说,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宣称人固有的利己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具有天然联系的人性论论点仍不过时被提及,尽管提及频率随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而不断下降。”【注: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2页】
(一)
迄今为止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是沿着物象拟制的工艺学路径进行的,从技术拟制到社会拟制,不断以研究对象“构筑-毁灭”的发展线索为依托,展示着改造与反改造的力量角斗,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这其实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于研究对象规定的一场反动的运动。反叛之路是建立物象拟制的社会工艺学。古典学家初步解决了社会物象关系“为什么”问题。利用知识论手段,新古典学家进一步举出社会物象关系的“是什么”问题,统一了社会物象规定,从而可能提出物象对象和物象关系对象的对接问题。新制度主义试图重归物象拟制的社会工艺学,但它的直接前提是技术拟制的社会工艺学,而提出物象关系对象的“如何来”问题。借助现象学的造饰,新制度学家力图从“物象”中提炼“物象关系”,而能够现实地提出物象对象和物象关系对象的对接问题。
新古典学家由知识论角度,提出“生产”(工艺学对象)改造为“物象”(拟象的工艺学对象)的方案,真正启动了研究对象的变轨运动。但其未能解决工艺学的“生产”何以能够成为工艺学的“社会物象”。新制度学家虚假化唯物主义发生学,使现象学=解释学,终于寻到一条解决问题的出路,即物象关系从物象中生成。交易关系乃成为统领性的社会物象关系。这项方案致力于如何来、为什么、是什么问题的物象领域内的彻底解决,从而真正建构起“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物象拟制的不同类型。据此而论,新制度主义不可避免地将是隶属于新古典主义的改良主义运动。
由生产关系运动和生产关系构造的研究,全面撤换为物象关系运动和物象关系构造的研究,是新古典主义的使命。也就表明物象一般规定成长到了成熟的阶段。在资产阶级理论家看来,有关经济物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物象运动——由价格调节的资源运动的关系就代表了社会生产运动关系;从中取出的经济关系因而只能是各种物质要素实体之间的关系,即物象生产关系,至于消费者“选择”,可说是物象交换关系。这导致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内部的经济学革命,围绕“知识论转向”进行。这形成了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攻击。
一种极为庸俗和低劣的想法是:“马克思之所以走向歧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相信,他可以在字面上讨论那些只能通过定量技术才能处理的问题。”以至于认为,作为一种全盘化的知识的理论,“就必须理解劳动价值论或利润率的下降是如何把我们引入歧途的。而且,没有一种微小的形式装置,是不可能证明经济问题的。”【注: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48页】
出于进一步巩固这种知识成果的需要,资产阶级学者就必须动用物象规定全面覆盖住古典体系和马克思体系中所有的有关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阐述对象。
存在论和知识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都依据某种本体论。但是,它们有不同之点。“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它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第42页】
简单概括:一者把矛盾显露,从而会引导对自身体系的批判和否定,一者则把矛盾隐藏,最终变“存在者解释”为“存在解释”;一个仍具有历史感,一个则只具有知识逻辑感。对于知识批判,马克思如此说:“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诠释而已”,而且,“同一个朗格在谈到黑格尔的方法和我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所说的话实在是幼稚。第一,他完全不懂黑格尔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第338页】
这是马克思对“康德式黑格尔主义”的工作揶揄。与此相反,列昂惕夫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正确性的获得是出于对历史的自觉。说那是仅源自他的个人天赋和工作直观,乃是误解;似乎是说:它带有浓重的马克思辩证法的个人特点。关于“活的历史”研究方法,列昂惕夫赞誉马克思:
马克思对历史的准确预言,不是来自分析技能,也不是谣传的方法论上的优越性。他的优处是具有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的经验性知识……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的性格阅读者。如同大多数人一样,马克思具有理性分析理论,但它们不会那么能够长久地站得住脚的。从而,一旦当那些不是对现实感有异常掌握能力的经济学家,同样试图在马克思蓝图的基础上跋涉时,他们会很容易地找到并指示出马克思理论的种种内在缺陷。而归根结底,马克思之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意义是那种对于直观的源源不断的准确性。【注:Leontief, Wassily. 1938: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8(1): 8-9】
这些根本印证了熊彼特的判断:“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为完成他的使命运用了一个武器,这就是掌握和支配广泛的有关历史和现实的资料。”不过,“他喜欢某种形式的类推法,这可以在他和黑格尔的争辩中找到。他喜欢证明自己是个黑格尔主义者并引用黑格尔的语句。”“但仅此而已。他从未将实证科学引入形而上学的歧途。他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的是正确的。”由此,“分析他的观点,你不能证明其中有他自己的想象,他的主张都不是源于哲学领域,而是建立在社会事实之上。”并且,“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玄学、艺术流派、伦理学思想、政治主张可归结为经济动机或者不重要,他只是要揭示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的经济条件。”据此,“经济史观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注: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7-9页】
卢卡奇则恰当地讲:
马克思的真正的方法……把全部存在理解和表述为一个就其基础而言是历史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只有认识并且承认,必须用整体在本体论上的存在优先性去取代“物性的”存在观,必须用对于充满活力的过程所具有的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性的认识去取代人们对这些过程所作的简单的因果性的解释,我们才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认识和阐明存在(当然首先是社会存在)的范畴问题。【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134页】
(二)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嘉图及其学派改造劳动价值论运动失败,则意味着效用主义(其数学用语即“边际主义”)将不可阻挡地兴起。“回顾19世纪70年代及其后的经济学发展历程……与其说经济思想被接受是因为它正确,被拒绝是因为它错误,不如说被接受因为它有用,被拒绝因为它不再有用。”【注: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杨培雷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第143页】
“渐渐地,人们越发不再依赖于基本假定的经验基础或其它基础,而是更多地沉浸在以那些因假定而变得简单为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过程中。”【注: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9页】
资源配置替换生产方式的位置,成为物象世界中社会生产运动的代名词;理性主义狡计的全部目的即是回到知识生产本身,重回形而上学体系。
【注:实质的工作内容是从资源配置中掏空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向度的规定。因为从虚假的二重性即物象二重性出发,使得外层的商品两个实存规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具有了统一的实体形式,即“抽象效用”。于是一方面,使用价值的运动由交换价值调节,由于这个功能,交换价值化为了“价格(形式)”,即均衡价格和价格波动;另一方面,调节使用价值运动的交换价值本身亦由它们的统一实体决定,迫使自身限定为纯粹形式的规定。整体过程于是在运动上显象为:静态的使用价值体系(抽象)→交换价值体系(运动中介)→动态的使用价值体系(具体)。这个工作图像勾勒了资产阶级资源配置理论的基本骨架。因此,在全部的实质性内容上,它的学名也就应该称为“虚假的商品二重性(理论)”。】
目的(无论满足感抑或幸福感)是形而上的,通过对目的、手段二位一体的知识论设置,到头来,竟然手段本身也被说成是“形而上的构造”。对技术的关心第一次胜过对生产制度本身的关心,从而,资本主义工厂内的活动得以全面刻画为生产技术上的关系,被描述为“生产函数”。
(然而)生产函数一向是错误教育中一个有力的工具。教给经济理论的学员的是O=f(L,C),这里L是劳动的一个量值,C是资本的一个量值,O商品产出率。学员所接受的教导是,所有工人都是一样的,L是用人时计的劳动来衡量的;还教给他于选择产量单位时所涉及的某些关于指数的问题;然后就急急忙忙接下去探讨下一个问题,希望借此可以使他来不及想到C是用什么单位来衡量的。【注: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顾准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85页】
资本者,乃是手段与工具。因此,要否定一个常识:“对于全然熟悉这一问题的人们来说,资本就是货币的同义词。”理由是,“资本与货币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不比货币与财富之间的共同之处更多;货币本身并不执行任何资本的职能,因为它不能对生产起到任何辅助作用,它必须通过与其它物品相互交换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任何可以用来与其它物品相互交换的物品,都可以在相同的程度上对生产做出贡献。资本为生产所做的是,提供场所、保护、工具和工作所需要的原材料,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供养并且维护劳动者。这些均属于现在的劳动需要过去的劳动以及过去的劳动的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任何具有这种用途——为生产性劳动提供各种先决条件——的物品,就是资本。”【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金镝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第30页】
资本一词,被用来概括所有可能的生产因素,它包括各种资本设备、正处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品和被生产出来的产品。资本被定义为用于将要打算生产的人造物品——包括所有的机器和其他生产装置。物理学理解异变为数学解释基础。社会物理学之变为数学物理学,意味了又一场的研究对象“变革”。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觉行动起来,对古典主义研究对象施以涂改的行为。而从李嘉图的方面来说,他已经“把无产者看成同机器、役畜或商品一样,却没有任何卑鄙之处,因为无产者只有当作机器或役畜,才促进‘生产’(从李嘉图的观点看),或者说,因为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生产中实际上只是商品。这是斯多亚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只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而且他在实践中也确是一个博爱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29页】
所以,卢卡奇要说:
在哲学的发展中,实证主义,首先是新实证主义,只有当它们要求在所有的世界观问题上采取一种完全中立的立场,让所有本体论的问题都悬置起来,成为一种把自在存在的全部问题作为原则上不可回答的存在问题从它们的领域中清除出去的哲学时,才具有这种特殊位置。实证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在这方面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遗产……19世纪康德的唯心主义消失殆尽,在实证主义中出现了一股唯心主义的潮流,一种不仅仅反对唯物主义的潮流,自负创造了一种哲学媒介,把一切世界图像,一切本体论都逐出认识领域,同时创造了——所谓的——认识论领域,它既不是主观唯心的也不是客观唯物主义的,却恰恰处于为纯粹的科学认识提供保证的中立之中……科学的普遍数学化迅猛发展,产生一种新的数学逻辑,语义学科学。新实证主义特别把数学逻辑包括在它“语言”里,并大规模地推广马赫-阿芬那留斯的中立地域,赋予它一种极强烈的客观的外貌,而不必与来自感觉“要素”的旧实证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决裂,因此,“形而上学”的论战出现了一种新的腔调……这一发展在新实证主义中达到了顶峰。全部认识论变成了一种语言规则、语义学和数学符号的转换信息、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工具。同时数学因素日益有力地强迫在客体与方法的转换信息上把重点转移到一种形式上无矛盾性的日益唯一的方法,客体本身被当作纯材料为转换信息的可能性来使用。【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399-404页】
(三)
因为,斯密与李嘉图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马克思对这条工作路线有时确实保持了沉默。阿尔都塞借机进行如下点评:
马克思权衡了他从他的先驱者那里得到的东西。他以两种不同的形式高度评价了他的先驱者的思想……一方面,他赞扬并高度评价某些先驱者确立并分析了重要的概念……另一方面,他强调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功绩,这个功绩涉及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成果(例如某个概念),而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他认为有两个不同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从所谓伽利略式的经典意义上说,就是科学的态度……经济科学对马克思来说就像其它科学一样取决于从现象到本质的归纳,或者像他用天文学作确切的比喻时所说的那样,“从表面运动向现实运动的归纳”……第二个特点:科学是这样一种系统的理论,它能够包括它的对象的整体并能够把握住将本质(归纳出来的本质)同一切经济现象联系起来的“内在联系”。
他认为在客观比较了斯密和李嘉图在科学上的不同之后,马克思的观点是:
斯密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就在于他试图把具有不同本质的对象归结为同一的起源,把真正的本质(已经归纳出来的)和尚未归纳出本质的纯粹现象看作是具有同一本源的。因此,他的理论就是两种理论,即现象论(没有归纳出本质的现象的集合)和唯一科学的本质论(本质的集合)的毫无必然性的结合……李嘉图的功绩在于他考察并克服了斯密的两种“理论”的矛盾。他真正地在具有科学性的形式上思考了政治经济学,也就是说把政治经济学看成是一个揭示其对象的内在本质的统一的概念体系。【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90-91页】
根据这样的判断:李嘉图跟随斯密以物理学诠释社会现象,试图建立揭示“本质”的社会物理学。这就为后来的数学物理学提供了分析基础。李嘉图毕竟不同于斯密,他直接拥有亲自然主义学说的立场与方法:
尽管历史决定论基本上是反自然主义的,但它决不反对认为物理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两者有着共同因素的看法。这也许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者一般认为社会学同物理学一样,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其目的都是达到理论的和经验的知识……即社会学是一门理论学科,意思是它必须借助理论或(它试图发现的)普遍规律以解释和预测事件。而所说社会学是经验学科,乃是指它得到经验的支持,它所解释和预测的事件是可观察的事件,并且观察是接受或否定所提出来的任何理论的根据……其实应该反对的是对这种观点的发挥,即它们包含有其它的假定——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尤其是有关历史规律或趋势的学说。【注:Karl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The Beacon Press, 1957), p. 35-36】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李嘉图的真实区别在于学科基础严重不同。马克思要说明的是以历史发生规定为基础的一种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他把人类生产的发展趋势同物质运动规律(作为“表现形式”)在构造上结合起来,合称为“社会运动的自然规律”。但这种运动规律不过意味着对单一空间发展结构的反叛,因而是价值规律的历史过程,是价值的具体社会实现过程。因此,数理学派没有从劳动过程中看到“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理性(活动)支配着手工劳动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过程的历史过渡,冥冥中起着作用:机器把“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它的物。”这样,“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209页】
李嘉图跳过商品生产的理性运动的必要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必然就为强行取消矛盾的那种科学即物象学铺平道路。这样,配合着庸俗化的三位一体公式(其源起于斯密教条),形式化的三分或四分的叙述体系出炉了。这种强制自然带来逻辑上的左冲右突,“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无休止地追逐公式。”
【注:斯密教条是三位一体公式的原罪。原罪的原罪则是斯密对于抽象市民社会的认同,从而导致把资本主义生产秩序视作绝对的最后形式。】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第155页】
实际旨在撤销历史研究基础,一笔勾掉历史对象地位,不断为零乱思想寻找合适的知识买家罢了。
理性主义的“狡计”
从新古典学家的眼光中流露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不屑:他们将理论基础羞答答地建基于“伪自然主义”,同时宣布自己是“社会唯物主义”。于是罗宾斯干脆宣称这一定义: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这是在纯粹的科学标杆上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的诠释——利字当头,而排开了“向善之心”,丝毫不顾及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特性。这是对资产阶级而言的“激动人心的”经济与政治截然分开的历史时刻。
【注:“罗宾斯给经济学下的定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在于他的定义条理清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他所描绘的市场经济中,总量波动并不严重,长期增长是经济历史学家而不是理论家的课题,经济学家主要应分析和观察自发过程。在对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之后,资源配置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占有突出地位。罗宾斯的观点还有一个令人愉快的特点,那就是将经济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化了。一旦摆脱了古典学派对政治目标进行的那种旧式探讨,一旦摆脱了那种对资源供应与技术进行半社会学的研究,经济学家便可以完全像科学家那样在一个他能驾驭的有限领域内大显身手。”(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317页)】
(一)
将古典主义称为前科学,对应地把新古典的自身称为科学,把新古典之后称为后科学,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古典主义持有研究对象的经济政治的合一观,但同时为历史研究对象(国民财富的性质)转为物象研究对象(国民财富的原因)的研究转向做好了准备,并打算好了要论证物质生产的“知识的本质”。对应把古典主义称为前物象科学,将新古典自身称为物象科学,而把新古典之后的制度主义运动称为后物象科学,似乎更显妥当性。前者是政治与经济的逐渐分离,中者是绝对的分立,后者是二分法研究基础上的对于资本的政治属性的粉饰。
【注:“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经济社会观、理性经济人假设和个体主义原则是紧密联系的。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坚信,经济世界是理性的,其‘自然秩序’是,经济社会的一切事物均处在严格的逻辑秩序中,而且按精确的数学规律合乎逻辑和理性地运动,其运动的轨迹是有序的、稳定的、确定的。同样,这个世界里的活动主体也是理性的,他们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进行选择和行动,他们总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动,而且能够以最合乎目的的方式行动。这样,从原子式的理性个体——经济人出发,借助各种辅助性理性工具(如数学方法),经济学家便能够在其行动的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推演出种种更为具体的理性行为模型;在这些较为具体的模型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就能较便利地解释或预测理性个体在特定情景下可能采取的具体行动,同时演绎出这些行动的社会总和所导致的一般社会状态和整体图景。因而,以理性方法建立起来的主流经济学就是‘事物必然是’或‘应当是’的知识,从而就是‘科学的’。”(胡乐明:《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批判》,载程恩富等主编《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第209-210页)】
【注:其间,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的发展为例,王亚南径直称之“是晚近资本主义各国为了稳定其金融统治或世界统治所促成或育成的辩护经济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619页)】
它迫使我们要理论承认:“卢卡奇……由于不能对斯密经济学的哲学内涵做出准确地解读,因而,对李嘉图与斯密经济学观点的哲学价值的不同也不能做出准确地把握。”理由据说是这样的:“立足于德国近代哲学的思路,而不是立足于古典经济学本身的思路,斯密与李嘉图两人的经济观点的哲学意义必然是一样的。因为,一旦把斯密与康德并列,那就说明英国古典经济学中的那条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性理论线索被遮蔽了。既然这样,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上李嘉图对斯密观点的推进这一理论层面自然也就不可能落入上述那种研究者的理论视域。”实际上,诱导我们拒绝这样的正确看法:“在卢卡奇看来,康德哲学中人不能认识和改变的‘自在之物’与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思路是一样的,都具有拜物教的性质。所以黑格尔对康德的超越,马克思对斯密和李嘉图的超越都是用‘历史’来代替了‘物化’的思维方式。”以李嘉图为例,古典主义作为前物象科学就在于:“在出发点上就显得唯物主义得多。他不以任何的假设条件为前提,而是直接以财富的稀少性作为自己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当然,“李嘉图只是对这种真实的社会关系作了量上的分析,还没有深入到质的领域”,相反,“由于卢卡奇始终是从相对于‘拜物教的对象性形式’,即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意识的角度来理解存在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中的‘真正的对象性’的,也就是说,他始终是从自然性的退却,人的特性的上升的角度来理解人的‘社会’和‘历史’性的,因此,卢卡奇在对社会关系概念的分析上即使不像斯密那样把它理解为假设条件下的抽象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他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内在本质的挖掘。”【注: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115-123页】
以上说法可以视为从科学方面对李嘉图的赞誉,不过,也必是过誉了。与此不同,新古典主义作为物象科学则在于建构“物自身的”经济学:可称之为纯粹经济学,或者以揭示物象本质为工作取向的经济科学。理由是:“有限的认识不但允许对象表现它自身,而且同时也必然地(因为有限)遮蔽它,而且这种遮蔽是如此的深不可测,以至于‘自在之物’是完全无法被认识的。因此,康德说,‘自在之物’是隐藏在‘现象之后’的不可知的东西。”亦即,“说人类作为有限的认识者只能认识一种‘纯粹的现象’绝不是质疑讨论中的存在者的现实性,而只是坚定地否认一个有限的认识者能够以一种无限的方式去认识把握一个存在者本身。”所以,“无限者”(理性的化身)必须代替“有限者”(有限的认识者)完成对“无限对象”的考察,即是说,“无限的认识与有限的认识所认识的是同一个存在者。一个认识的是自在之物,更准确地说,无限的认识让存在者出场、成为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无限的认识创造了存在者;一个认识的是现象,存在者在自我的显现中站立出来与认识者相对而立成为对象。海德格尔由此解释了康德关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的区分,他说:‘一个存在者有双重特征:作为自在之物和作为现象,这两个特征对应着两种存在方式:这个存在者处于与无限的认识的关系中,能够获得它的起源,同一个存在者处于与有限的认识的关系中:能够作为一个对象。’”亦即是说,新古典主义要完成一种绝对意义的本质经济学,即物自体的本体意义的经济学;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纯粹和超验的,无法和经验并行不悖。“先验知识不是研究存在者本身,而是研究先行的存在领会之可能性,这同时也意味着:研究存在者的存在机制。这种存在机制涉及纯粹理性对存在者的超越(超越性),只有在这时,存在者才能作为可能的对象来使经验得到衡量。”因此,“有限理性的超越就是先验演绎的基本目的”,“存在论认识的内在可能性的问题无非就是超越的揭示。”【注:孙冠臣:《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57-163页】
(二)
该拷问“理性”的特种经济学,必不可少地涉及到李嘉图的先驱性工作:
李嘉图确实宣布了生产对分配和消费的支配地位……李嘉图指出了达到对剩余价值现实的认识的一切外在征候,但是他总是在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形式上谈论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用不同于剩余价值概念的其它概念来谈论剩余价值。同样,李嘉图也指出了达到对生产关系存在的认识的一切外在征候,但是他却仅仅在收入分配和产品分配的形式上来谈论这个问题,因此他没有得出这些关系的概念……从整个过程看,马克思似乎把自己的工作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方面马克思满足于对自己先驱者的著作进行替代性阅读,他在这方面很“宽厚”(恩格斯语),这种宽厚态度总是使他过多地把自己的发现归功于先驱者,实际上把“生产者”看作是“发现者”,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不同场合,在涉及到他的先驱者生产出来的事实的概念含义时,对他们由于自己的盲目性而得出的理论结论表现出了严厉的态度。当马克思极其严厉地批判斯密或李嘉图没有从剩余价值的各种存在形式中区分出剩余价值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指责他们没有赋予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事实以概念。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简单的名词的“省略”实际上是一个概念的空缺,因为一个概念的出现或空缺决定着一系列的理论结论。
马克思的确很宽厚,部分容忍了李嘉图对于理性的推崇和自由探索。因为李嘉图认识到(仅从主观批判这一角度,可以这么说):“结构对于它的作用来说的外在性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外在性,也可以理解为内在性,唯一的前提是,这种外在性或者这种内在性应该作为不同于结构的作用的东西被提出来。”“这种区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常采取古典的形式,即内在和外在的区别,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事物的现象‘外观’的区别,事物的‘内在’关系、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同一些事物的外在关系、外在联系的区别。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对立原则上可以归结为关于本质和现象的古典的区别,也就是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区别,这一区别把存在本身和现实本身的内在的东西即它的概念置于存在本身之中,置于现实本身之中,从而把存在和现实本身同具体现象的‘外观’相对立,这一区别把不是属于这一现实对象的区别即层次或者各个部分的差别移入现实对象本身之中,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把这一现实的概念和认识同作为现存对象的现实区分开来的区别。”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对立在马克思著作中可以归结为一个明显的道理:如果本质与现象没有差别,如果本质的内在与非本质或现象的外在没有差别,那就不需要科学了。”
可见在这里,新古典很大程度上是模仿了马克思,换言之,他们——这些新古典学家敏锐捕捉到,理性本质不过是资产阶级期盼的抽象生产关系的认识和概念。但是对于这些新古典学家,阿尔都塞要怎样说呢?
马克思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范例。马克思由于彻底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可以表述如下:通过何种概念人们可以思考新的决定类型,也就是刚才论证的由区域结构决定这一区域的现象?更一般地说,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一切后果由这一结构的作用决定?进一步说,用何种概念和通过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从属的结构由支配的结构决定?或者说,如何说明结构的因果性概念?【注: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194-195、216-220页】
(三)
可如果要问新古典的概念究竟具有怎样的理论实践形式,就得追寻它的构成内容和工作来源。它的科学前提是:
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如此沾沾自喜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杰里迈亚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704页】
这位杰里迈亚先生严重缺乏历史知识:不知道在每一历史时代产品总具有具体的特性,不晓得这才是产品“效用”的经济规定,而妄图用统一的主观因素去尺度它们。马克思嘲笑这种把存在当理性、把理性当本性的无聊推理。以存在拟制存在者和以存在者限定存在毕竟严格不同。其显著的特点即在于需要排除“理性恨”规定(它在古典体系中尚存)。为此,“康德区分了‘自然主义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按照前一种方法,只要凭借自己的‘普通理性’,无须通过科学的途径就能对形而上学做出严格而有效的探索。”康德批评说:“这是赤裸裸的理性恨,它被应用到各种原理中,而最为荒谬的是,它把忽视一切人为的手段誉为扩展知识的一种独特的方法。”从而,“不难看出,康德这里所说的‘理性恨’,是指以自然主义的方法探索形而上学的人们,对任何具有科学倾向的理性思维的憎恨。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人并不憎恨理性的一切表现形式;事实上,在他们看来,普通理性就是思考形而上学问题的可靠的出发点。”【注: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
在物象视角下,交换关系成为自然品格的效用函数形式,作为生产函数的对称性的表现关系。于是,生产关系成为一条条客观曲线(成本和供给曲线),交换关系成为一条条主观曲线(效用和需求曲线);它们——这些曲线——仿佛不由货币或资本形式构造而出,而恰恰由物质过程本身构造出来,仿佛这是一项工艺常识。
于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推托不知道法律’。——按照经济法的假定,每个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注:《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2页】
以至于康德发出慨叹:
于是,关于形而上学也就有如下问题:作为自然禀赋的形而上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纯粹理性向自己提出、并为自己的独特需要所驱动要尽可能好地回答的那些问题,是如何从普遍的人类理性的本性中产生的……因而要么可靠地扩展我们的纯粹理性,要么设置它的确定的和可靠的限制。从以上普遍的课题产生的这最后一个问题,有理由是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因此,理性的批判最终必然导致科学,与此相反,理性不经批判……导致怀疑论。
这意味着科学(推理)必须具有一可靠之起点,乃是有关于纯粹理性批判之理想。假设是这个理想规定的“化身”:
在一种先验逻辑中,我们把知性孤立起来……从我们的知识中只突出思维仅仅在知性中有其起源的部分……因此,先验逻辑陈述纯粹知性知识的各种要素和在任何地方要能够思维对象就不可或缺的原则的部分,就是先验分析论,同时也是真理的逻辑。因为没有一种知识能够与这种逻辑相矛盾,却不同时丧失一切内容,也就是说,丧失与某一客体的一切关系,从而丧失一切真理的。【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43、82页】
这样,物自体来到人间,作为了每个人的常识,乃至是先验分析的可靠出发点——“假设”。“它剥离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纯粹的演绎推理加上数学公式,完全无视历史、社会学、哲学和制度框架。”也就必须为此承受这样的指责:“它是在不现实的、甚至是错误的假定下进行抽象的思考,建立抽象的模型。”【注: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第91页】
它最终完成一种颠倒:“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马克思揶揄说:“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自以为有深刻的批判力、发现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为他们作证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于是,马克思干脆直接挑明“经济学家是怎样说出商品内心的话的”,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话:“‘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注:《资本论》第1卷,2004,第101-102页】
(待续)
【许光伟,江西财经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和学术主攻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方法论研究。本文系《保卫资本论》第9章,载2017年修订版,第214-236页。】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