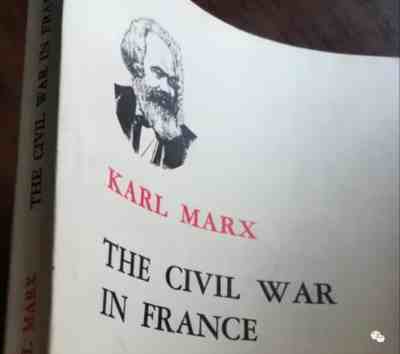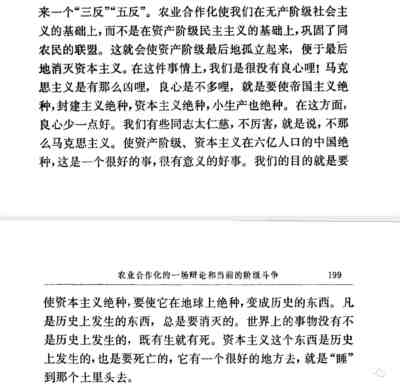俄乌冲突引起的国内舆论战发酵至今,我深深感受到了绝大部分国人的善良,或仁慈。
假如作为一种纯粹个人主观的东西,这无可厚非;但,假如这成为一个阶级当中不少人的集体迷误,那就很成为问题了。
的确,不论是挺俄还是挺乌,这种做法都意味着轻易把自己代入进去,而这种主观代入乃是真正马列主义科学分析之死敌。
我不禁想起了伟大的马克思。
有人责怪说:是马克思造就了左派“好斗”“偏狭”的特性,使无穷无尽的内部分化成为左派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
每当看到这种庸人的论调,我都禁不住嗤之以鼻。
的确,表面上看,马克思怼天怼地,除了一个恩格斯,甚至有西方学者说马克思对恩格斯也是不断试探,试探他是否能够以及多大程度接受自己的观点;庸俗的批评者所不知道的是,非如此,不足以树立起一种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新的思想体系,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马克思的“好斗”,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50年中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
而当今左方的基本问题,不是争论太多,而是根本缺乏真正严肃、科学的争论以形成对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共识,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马列主义对人,自由主义对己。
庸左们竟然跟右派一样对“扣帽子”有着无穷的恐惧,殊不知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害怕扣帽子,只是要求把帽子扣对、扣准。马列毛导师的著作,难道不是“帽子满天飞”??
列宁喜欢讲一个故事:列·托尔斯泰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蹲着,做出奇怪的手势。他断定这个人一定是疯子。走近的时候,他才相信这个人在做必要的工作:在磨刀石上磨刀。
庸人们则是远远断定他是疯子,还要加以放肆的嘲笑。
正是庸左们这种害怕争论、害怕分清是非对错的思维,庇护了小组习气,使得整个左方陷于无穷无尽的小团体分化。老实讲,光从舆论战角度看,不论是中间派粉红还是右派公知,都要团结和有技巧得多,他们在舆论场上带节奏的能力远胜于左方——因为左方在重大事件面前很难形成,或根本没有统一的观点去输出,无法迅速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叙事去吸引人们尤其是中间派的人们。各说各的、各自为战,就严重削弱了存在感。而在21世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当今时代,假如连舆论战主导权都不能掌握,庸左们哪怕重复一千遍导师“改造世界”的格言,也是对这句话的疯狂嘲讽而已。
当前左方的问题不是内部斗争,而是根本没有严肃的有意义的内部斗争。
恩格斯在他的晚年中,同样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做了坚决的斗争。读一读他尖锐的,甚至是刻薄的话吧:
“如果你们以为你们的那些小针头能够刺穿我这一层又老又厚的硬皮,那你们就错了。”
“你简直想象不到德国人幼稚到何等地步。”
“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也许这会把他们的病医好一些时候。”
“德国在平静时期一切都变得庸俗了。在这种时候,法国竞争的刺激是绝对必要的……”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我不禁想起了伟大的列宁。
要知道,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布尔什维克制定的政策路线,堪称惊世骇俗:他居然能够冲破多少年来人们根深蒂固的也是陈腐的民族主义观念的束缚,丝毫不怕自己生前身后背上“叛国”之罪名,极其坚定地指向一个目标:革命夺权。这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最伟大也最冷峻的人物才能有的作为啊。
我也不禁想起了伟大的毛教员,在农业合作化中的作为。
他说:“……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看似老生常谈,却是历来阶级斗争的伟大经验之谈。
不错,美帝霸权穷凶极恶,非推翻之不可;我甚至相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美帝国主义及其霸权体系又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
换言之,现实中很难再有哪个垄断资本,能够复制美帝的这种深入触及人们灵魂的极致PUA体系:美帝使大半个世界都匍匐在它的脚下,使东西方无数无产阶级成员对它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深信不疑顶礼膜拜。我相信,假如有一天这样的霸权都能崩塌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东西方大多数无产阶级都能认清资产阶级价值观的PUA本质、从而投身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实践了。
当我看到美帝头子在国情咨文演说中毫无表演痕迹的“大义凛然”的表演,听到他胡扯什么普京的坦克遇到了乌克兰人民——他所自信的绝对不是人民自己的力量,而是美帝价值观对人民的洗脑控制程度。
然而,有人不是这样估计问题:他们天真地以为,仅凭俄罗斯这样除了核弹头数目以外孱弱无力的次级资本霸权,就能真正撕开美帝霸权体系的口子,从而动摇整个霸权。乌克兰亲美傀儡政权能够怂恿起乌克兰人民进行顽抗,并非由于泽连斯基这个政治小丑有什么英雄的魅力,都是美帝洗脑之功:当无产阶级真的把什么“自由民主”当回事,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充当美帝维护和扩张霸权之炮灰,而不是自己组织和行动起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换言之,能够真正给美帝霸权以致命一击的,决不是其他资本强权的看似有力的挑战,而只能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觉悟、组织和行动。而在这样的觉悟、组织和行动看不到多少影子时,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当前仍是资本主义的黑暗而漫长的中世纪,红色幽灵的再降人世将取决于火种保留而不被扑灭。
正如伟大的列宁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所教导的那样:
“社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并不是偶然的。”
只可惜,左方庸人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不是捍卫理论基础,而是瓦解理论基础,把它降低到民族沙文主义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水平上去。
假设只讲“民族”,那肯定讲不过粉红;假设只讲“自由”,那肯定讲不过公知。其结果,就只能是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被牵着鼻子走。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