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列宁同志有两句名言,从我们的角度看,也是格言:
“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见于同一篇文章,1913年《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这两句话的理解问题。
毫无疑问,敌人,无论帝、修还是反,是不会喜欢这两句话的。敌人不仅排斥我们的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而且,他们还排斥列宁所赋予它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留情的表述形式。列宁使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充分革命化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似乎一部分同志、一部分统一战线朋友,对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连同它的列宁主义表述形式,也不是很理解、接受。“这怎么回事?列宁怎么说出这个话?是不是太‘绝对’、太‘极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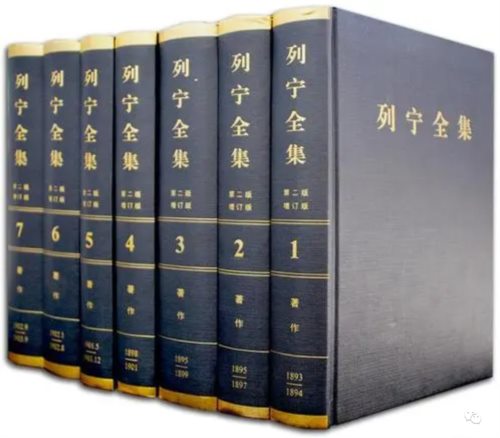
是的,如果从过分严谨的知识分子“挑刺”的角度看,是可以挑出刺来的。我们的朋友可以从孔夫子引证到罗尔斯,以证明“非阶级”的政治学说也不全是“胡说八道”,证明我们对非阶级的其他“社会主义”、非阶级的政治学说也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问题是,列宁不是任何“过分严谨的知识分子”。他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必须按照革命家的语言理解他的语言。
另外毛教员的一段话,也是强调“阶级”的,也得到了类似的“待遇”——修正主义走狗文人煞有介事地将其称作“极Zuo”思想的滥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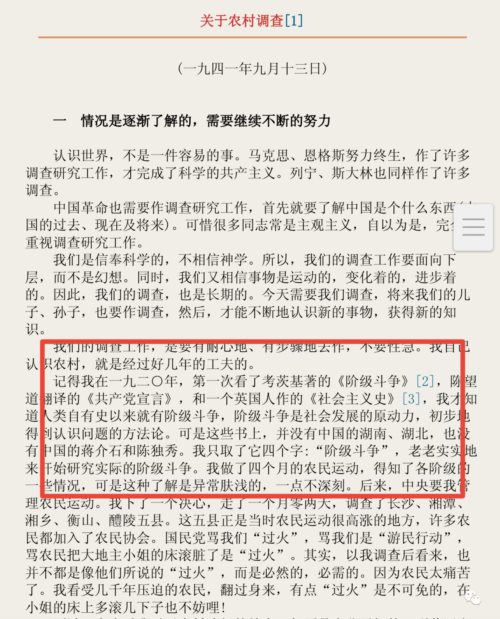
(载《文集》《农村调查文集》)
敌人的逻辑是可笑的。对阶级社会,你不做阶级分析?讲马克思主义,你不讲阶级?……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不等于它的阶级观点;那么,应该说离开了它的阶级观点,马克思主义就要大打折扣、面目全非。不错,这确实是“一部分”,但却恰恰是至关重要、关系灵魂的一部分。你说丢就丢了,那主义还算什么?还能存在吗?
敌人的伎俩就在于:只承认是“一部分”,不承认或变着法子否定是“关键”甚至“灵魂”的一部分,把关键的、灵魂的一部分给抽掉——从而“肢解”了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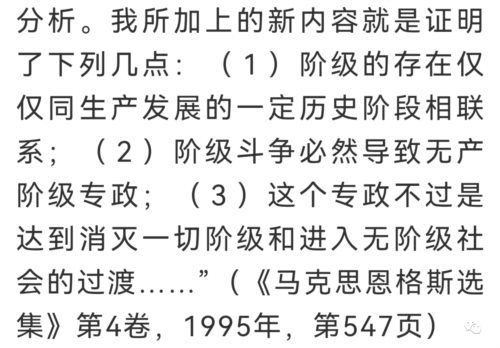
甚至对于不少公认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论断,他们,只要愿意和有时间,都可以这样来“挑刺”。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书呆子会说:怎么只有“枪杆子”,党呢?群众呢?……假如处处要做这样的“挑刺”,那么应该说,马克思主义(马列毛主义)似乎到处都能找到这样的话,似乎我们对它的相信就动摇了。
我要说,必须认识到:这正是一部分狡猾的敌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独出心裁的“手法”。敌人早就学会了一点,那就是不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是拐弯抹角、打着“学术研究”“理论研究”“补充完善”“反思”“再评价”“重解”等等貌似正确的旗号,来进行诸如此类的“挑刺”。
不顾它的精神实质;拘泥于它的字句或表述方式;玩弄字句、概念,最终达到否定被实践证明了的革命真理的目的——请看,这是敌人的一类处理“手法”。而我们自己——马克思主义者,假如也是这样变成字句或表述方式的奴隶,不去关心、把握它的主要意思、精神实质,那么,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其中有的注定要掉进学院派反革命的“知识陷阱”里去。
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应该给自己提出要求——不要掉进字眼里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里说的“枪杆子”,毫无疑问,当然是指的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枪杆子;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说明“什么样的”枪杆子,而在于强调武装斗争,自然是、默定是革命的武装斗争对于夺取政权的意义。重点在这里,不在别的地方。
一切非阶级的政治学说、非阶级的社会主义都是胡说八道——这句话的重点呢?在告诉我们:阶级很重要,阶级分析很重要。这是用典型的列宁式的鲜明风格提出问题,以引起读者的充分注意。照我说,这正是列宁的长处、伟大之处。
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作为“这一派”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眼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假如我们对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中活动时,竟然不搞阶级分析,竟然不懂得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一切东西,甚至于要变着法子回避阶级问题——假如这样,那就是天大的犯罪,就根本称不上是什么“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按我理解,这句话的重点在这里,不在别的地方。
假如认为列宁不懂得马克思以前、以外的人类思想文化的意义,那就错了。因为正是同一个列宁,教导我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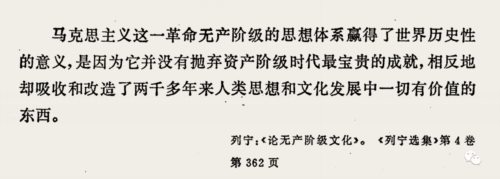
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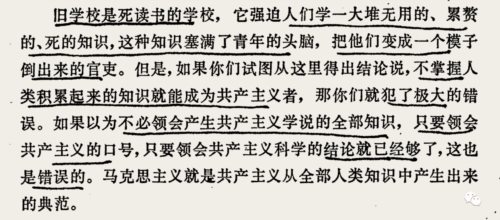
——《青年团的任务》
因此,怎么能够以列宁强调阶级的那两句话,来指责他“全盘否定”其他的学说呢?
不,不能够。
二
由对经典著作、经典论断的理解问题,我们不难发现——有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或说马克思主义观:
一种,正是拘泥于字句,拘泥于具体的表述方式,不去理解和掌握它的精神实质、它的基本原理、它的思想方法。从中,既可能产生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可能产生修正主义的倾向。是真诚的,但是拘泥于词句,就可能变成教条主义——面对实际问题,他就照搬,或者沉浸于历史的比拟,不做具体分析。
比方说,把今天产生的几乎一切问题都简单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半殖民地社会的国情相比拟,甚至一一对应……不懂得近半个世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懂得当代社会的新变化,以至于照搬式地提出所谓“第二次新民革”的要求。这表明,有的人完全不懂得70年代末以来的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形给我们提出的关于革命阶段的要求,完全不懂得。

他们读《毛选》前四卷,甚至很熟悉,但方法不得当。不是掌握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今天的情形,而是学了就到处做一个“找相同”的游戏:谁是A,谁是B,谁是C……殊不知,假如A、B、C都是只有在半殖民地那种国情下才能存在、成立的东西,那么,怎么可以“移植”过来呢?!
据观察,这部分人还很喜欢批“教条主义”,实际上他们那里正是教条主义的重灾区。其思维方式、“研究”方式,用斯大林的话说,乃是典型的沉浸于“历史的比拟”,或模拟。
这当然是一种教条主义。

拘泥于字句,也可能产生修正主义的倾向。假如一个人是故意拘泥于字句,像我们前面讲的那类敌人的手法一样,故意把马克思主义关在字句、表述方式的牢笼里,把它庸俗化——这就是一种“修正”。比如,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夸大军队作用,硬说列宁那两句话是“全盘否定”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就是一种恶劣的“修正”,完全歪曲了导师的本来意思和强调的重点。
当然,也可能不是敌人,而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又犯糊涂的人。实际上,一个人只要接触马克思主义,只要需要处理自己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那么,就可能产生一些认识上的不良倾向,比如教条主义,比如修正主义,这也是正常的。解决的办法恰恰就在于,要学会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表述,而是抓住它的精神实质、基本原理、思想方法,特别是学会用它的方法去分析、解决今天的问题。——这正是另一类马克思主义者,或说列宁-毛主义者的态度、做法。

另一边,第二国际、孟什维克,我国历来的机会主义者,无一不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出了问题,在方法上出了问题。
包括今天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左派”,以及“学院左派”,也是如此 。仔细观察他们是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兼而有之,炖大杂烩,该搬的时候搬,该“修”的时候“修”……某种意义上,马列毛主义属实被他们“玩”(糟蹋)明白了。
三
在思想、认识方法上,使人感到,他们存在以下思维短板:
①主观主义,过于浓厚。总是拿自己的主观感受、主观体验代替对事物应有的客观分析,甚至代替客观事物本身。
美帝是万恶的,要蔑视、鄙视、仇视美帝国主义,要憎恨它——这个感情是好的;但因为这个感情,好像跟美帝又勾结又矛盾的赫、勃“修”派,以及袁大总统、张大元帅、蒋大队长之流,就变得眉清目秀了,就要给洗白——这就叫主观感情压倒了科学认识、科学分析,好东西变成坏东西。

②不讲辩证法,不懂辩证法。但凡真懂点辩证法,就不会对“革命中立主义”的提法感到大惑不解。现实是,有着各种各样的中立,好比有各种各样的妥协;我们的态度是,具体分析它。“革命中立主义”是哪种?——是“中立”于两派资产阶级之间,决不是“中立”于无、资之间,也并不排斥利用、乃至统战一部分资产者(前提是:站在自己立场上!)。
这种“中立”形式上是“中立”,实质上也并不“中立”,是“独立”,是坚持站在最广大无产者的立场上看待、分析问题并制定策略,是坚持无产阶级在运动中、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性和领导权。“革命中立主义”当然是列宁主义的东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不要统一战线一样,才是反列宁主义的东西。
③“不读书”主义。说得文雅一点,叫“理论取消主义”。也就是说,他们那里存在着一种反理论的倾向。所谓“不读书”,就是不要科学理论、取消科学理论,可能口头上宣称自己“接受”马列主义,实际是根本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就是说根本不会运用马列主义活的灵魂、马列主义的方法去看待、分析事物。有的甚至自己不读书,还不许别人读书,谁读书就被打成“教条主义”。
有人是这样:文章前两句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往下看他的分析,没有多少阶级分析,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气味。哪有那么廉价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阿猫阿狗、鹦鹉或留声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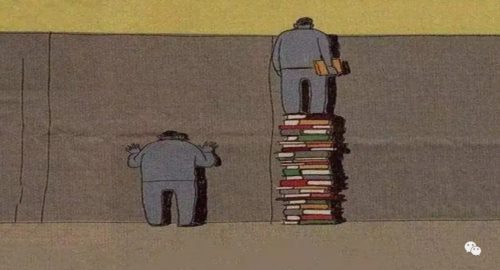
这是一种什么呢?这是一种程度较高的修正主义,或极端的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经验主义表现。
④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新民主主义的教条主义”。怎么又修正主义、又教条主义呢?一个人可不可能既犯修正主义,又犯教条主义呢?完全可能。教条主义的“精髓”是生搬硬套,不是说读书多就是教条主义,不是说引用马列毛经典就是教条主义,更不是说捍卫马列毛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教条主义。
我们有些人天天在那里“反教条主义”,其实是装模作样,他连什么是教条主义也不懂。跟赫鲁晓夫反“教条”差不多。既存在修正主义,也存在教条主义,当然前者——修正主义是主要的;而且他们有些人的修正主义发展得相当严重,已经表现为一种“不读书主义”(见上述)。
“(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教条主义”,有人犯的教条主义,主要就是这一种。什么意思?就是简单地、机械地把历史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概念、范式、策略等等,搬到今天来;甚至于,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所对应、所适用的半殖民地国情,也给直接搬过来了。
用刘继明老师的话说就是,“总是不加分析地将当下的一切国际国内问题,跟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际国内矛盾简单地进行比附,甚至把俄乌战争、中美冲突和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相提并论,并且机械地照搬毛主席的相关论述进行解读”。
总之,这些显示出:他们的思维方式,受四十多年来大泛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方法渗透太厉害,以至于对马列毛主义的分析框架、分析范式,或基本方法,茫然无知、不会运用。要说“西方渗透”,那么,这些人的大脑,就是被西方、被西方资产阶级严重渗透的一个典例。恕我直言,对方的大脑,可能已经被渗透成筛子啦!
四
这里面就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左派”之下的一个小小的派别,或许能叫它做“学院派”的——据观察,是颇受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并且,给人感觉他们对于新马、西马的东西,也并没有很好消化,而是“拿来”就用。
假如盲目地机械地学着一些新马、西马学者的样子,连苏、中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性质(修正主义以前时期)都要否定,以及跟在第二国际、孟什维克、现代修正主义者屁股后面指责列斯毛把社会主义“搞早”“搞坏”了——假如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朋友就走得太远了。不错,我们和学院派朋友都承认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需要总结,但不是这样一个“总结”法;并且要从赫、勃的“修正”演变开始总结起,才是科学的。
从这类朋友的叙事中,就产生出一个巨大、人为制造的缺口:马恩、列斯毛之间被隔断了,甚至马恩之间、马列之间、列斯之间、斯毛之间也被隔断了(即,夸大他们之间的差别性),国际共运的历史传承性变得支离破碎了。当然,这其中有的人要对接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传统——既然如此,那么,就让他们去作吧。
我们的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已经成为一条公认的真理;问题还有,它是“怎样的”一种行动指南?——从朋友的思想方法看,我觉得,很难说他们懂得。
出路在于:根据、运用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详尽占有材料,弄清楚(即不是一知半解地“了解”)当代阶级关系、社会性质。然后,才谈得上“改造世界”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在实践中、在理论总结方面开拓马列毛主义的光辉新境界。
正在展开的历史时代,必将再次证明:只有列宁-毛主义者,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真正继承者。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