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艺作品中出现的“还乡团文学”现象,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与意识形态博弈的具象化表现。从《软埋》到《生万物》,这类作品通过重构历史叙事,试图消解土改的正当性,其背后存在三重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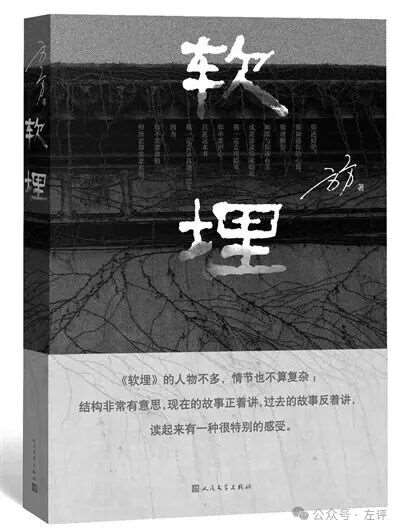
一、历史叙事的解构与重构
《软埋》通过“软埋”意象将土改中的阶级矛盾转化为个体命运悲剧,用时间遮蔽历史真相;而《生万物》则通过地主与佃户的情感纠葛,将剥削关系浪漫化为“人性救赎”,甚至塑造开明地主形象以弱化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这种叙事策略实质上是将土地改革从“制度变革”降格为“道德争议”,正如《生万物》导演所言“人物不做脸谱化处理”,但刻意突出地主“勤俭”一面却回避其剥削本质。
二、意识形态的隐性对抗
自上世纪80年代起,部分文艺作品持续否定土改的合法性。《生万物》与《软埋》一脉相承,延续了《白鹿原》《生死疲劳》等作品“美化地主、丑化农民”的创作路径。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解构土改史,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根基——正如《中国土地法大纲》所确立的“耕者有其田”原则,正是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三、市场与资本的合谋
这类作品常以“人性深度”“历史反思”为包装,迎合特定受众的猎奇心理。《生万物》通过爱情线稀释阶级斗争,实则是将严肃历史议题转化为消费主义语境下的情感商品。资本力量与文艺创作的结合,使得“还乡团叙事”获得传播渠道与话语空间,形成“否定土改—美化地主—污化农民”的闭环逻辑。

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暴露出历史蜕变与文艺批评失语的双重困境。正如《生万物》争议所示,当“地主闺女下嫁穷小子”的桥段成为叙事焦点时,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的正义性已被阶级调和悄然置换。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