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7月中旬,正是武汉酷暑炎热的高峰期,我意外地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对方自我介绍说,他是德国科隆大学的一名博士,名叫蒂洛.迪芬巴赫(Th Diefenbach),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刚刚获得一项由德国弗里茨.蒂森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课题“刘继明与文化关怀小说”,此次来华主要是为了收集相关资料和拜访我本人。他还用吐词清晰却偶尔有些不连贯的普通话说,为了找到我,他费了不少周折,原以为我住在上海,到了上海后才知道我在武汉。他还是通过一家出版过我小说的出版社打听到我的电话的。
几天以后,蒂洛.迪芬巴赫就从上海飞抵武汉了。当我在天河机场出口处远远地见到一位身材高挑的外国小伙子,拖着一只装有滑轮的大皮箱,对着接站的人群左顾右盼时,我知道,他就是蒂洛.迪芬巴赫了。果然,当看到我拿着写有他的中文名字“江灿”的小纸牌后,他便迈着大步向我走来,老远伸出手道:“您是……刘继明先生吗?”
这就是我和蒂洛.迪芬巴赫最初见面时的情形。
他显然比我预想的要年轻许多,约莫30岁左右,比我小十多岁,属于“下一代人”了。像这个年龄,在中国文化界有个特殊的称谓:“70年代人”或者“新新人类”,代表着上世纪90年代后在中国兴起的一种流行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服饰和外表看上去,蒂洛.迪芬巴赫与当前中国随处可见的青年人也相差无几:一身黑色的T恤和牛仔,活力四射,透露出他这个年龄的人崇尚标新立异和“酷”的生活趣味。但那双深陷于高耸的眉骨下面的蓝眼睛却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沉着、冷静、敏锐,带点儿探究事物和长于思考者的好奇,使我不由想到德国人特有的那种富于理性和思辩的传统。
我带着蒂洛.迪芬巴赫在我住所附近的一家普通宾馆住下了。似乎为了验明身份,刚安顿好,他就从大皮箱里翻出一沓关于那个研究课题的报告文本给我看,全是德文的,我当然一个字也看不懂,但从他作为附件夹在文本中间的作品复印件,我看清那是多年以前我发表在《上海文学》等中文杂志上的几篇小说。
蒂洛.迪芬巴赫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他拜访我的具体目的:除了为他的研究收集完整的资料,还希望与我商谈将我的《海底村庄》、《蓝庙》等小说翻译成德文的事宜。他还反复嘟哝,说本来要向上海的朋友借一台录音机,以便录下我们的谈话,供他日后写论文参考,但临动身前却忘记带上了。后来,我倒是为他借了一台笔式的微型录音机,却没派上什么实际用场。因为我发现,虽然蒂洛.迪芬巴赫的中文口语比较流畅,应付一般的日常会话绰绰有余,可如果进行复杂的交流,就显得有些费劲了,再加上那支录音笔操作起来不大方便,不是中途卡壳,就是交谈了一会儿,却发现什么也没录进去,倒腾来倒腾去,两个人都觉得麻烦,甚至把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兴致也弄没了。我们只好不约而同地扔下那个玩意儿,并且像卸下什么重负那样松了一口气。
我没有出国考察或旅游的经历,对西方(人)或欧洲(人)的认识,完全依赖于自己有限的知识背景,因此,我对蒂洛.迪芬巴赫了解或探究的兴趣,丝毫不亚于他对我这个“研究”对象的兴趣。在随后的两三天里,我们的交谈与其说发生在访问者与被访问者之间,倒不如说是两个新结识的朋友,抛下各自相异的文化身份之后,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闲聊。况且,我们的交谈始终是在吃饭、喝茶以及在珞珈山和东湖边漫步的过程中进行的,没有半点儿正襟危坐或故作高深的严肃状。我想,这才是交谈的愉悦所在。这样,刚见面时作为“文化符号”的迪芬巴赫或江灿,便开始以一个活生生的个人走进了我的视野。
蒂洛.迪芬巴赫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老迪芬巴赫先生毕业于著名的法兰克福大学,精通希伯来文、梵文等七八种外国语言,曾长期担任中学校长,属于上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青年时代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富于反叛精神,对席卷全球的反官僚和等级制度以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怀有某种近乎亲缘般的认同感。但到了70年代,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上台后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像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老迪芬巴赫先生也逐渐放弃60年代的激进主义立场,加入到了重新占据主流的右翼行列,像所有老派的德国人一样,变得因循守旧,安于现状,退休后,他举家搬回距法兰克福不远的家乡小镇,在远离尘嚣的市郊过起了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但“60年代”的文化因子仍然根深蒂固地依附在其内心深处,并且时时影响着他对时事的判断。比如他始终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热情关注中国的发展,醉心于收藏中国文化典籍,将毛泽东时代同包括平等、公正等在内的一些政治文化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狂热追求过的社会理想),而对于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他的态度是怀疑、抵触,“颇有微词”的,他认为,虽然今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却导致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并且是以断送毛泽东时代经过艰苦努力形成的平等公正的社会形态为代价的。他甚至数次拒绝了到中国观光的机会,而他青年时代最大的愿望就是亲自到中国感受一番……
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老迪芬巴赫先生的观点也许够偏颇固执、不合时宜了。但他对信念和理想的执著维护,或多或少影响了蒂洛少年时期的成长,很早就对中国产生了某种神秘感和好奇心,以至于中学时就开始学习中文,上大学后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学专业。谈到这种选择,蒂洛是这样对我说的:“其实,最初我并不是想将来做一名汉学家,仅仅是出于‘超越’我父亲的冲动。因为他懂那么多外国语言,在这些领域我根本不可能超过他,以至我常常在他面前有一种自卑感。而他虽然经常把中国文化挂在嘴边,却唯独对中文一窍不通。”蒂洛对我耸了耸肩,带点儿调皮地一笑。
他还告诉我一段有趣的经历:中学时,他狂热地喜欢上了流行音乐,想买一把吉他,但父亲不愿意给钱,表示希望他能够学习古典音乐,如果他想有一台钢琴,马上就能如愿以偿。但蒂洛拒绝了这个诱惑,报名参加了学校的学生乐队。后来,蒂落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校园流行乐手,他父亲虽然激烈反对儿子的兴趣爱好,并且使父子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但最终还是和母亲一起,观看了蒂洛的音乐演出。蒂洛谈到这件事时,显得很得意。这也使我看到了西方青年人身上那种勇于挑战和叛逆的个性。
“那么,你对毛泽东怎么看?”在东湖边的一家小酒吧里,我饶有兴趣地向坐在对面的蒂洛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本来想问你呢,没想到被你抢先了!”他抚掌笑道。不过,他很快低下头,沉吟了一下说:“毛主席是个伟大的人物,他使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统一的东方大国,影响了世界的进程。不过,我不赞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错误。如果他在50年代就去世,我想他会更伟大吧……”末一句,他的口气有点儿模棱两可。
蒂洛的观点同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倒比较吻合,这让我感到出乎意料:“你父亲赞同你的观点吗?”
“噢,当然不!”他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我们经常发生争论,到头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我们也没有想到说服对方。在这一点上,我父亲还是比较民主的。”他话锋一转,用挑战的口吻道:“刘先生,你呢,你怎么评价毛主席?据我所知,在中国,怎么评价毛,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
“是的。”我点头承认。但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坦率告诉他,毛泽东逝世时,我还在上小学。当我念完中学,直到后来上大学,接受系统教育的80年代后期至今,中国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和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潮都一直居于社会的主流,思想界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批判和清算,情绪化的色彩比较重,而真正理性的认识却很少见。我个人也不例外。但90年代之后,我的认识开始出现了一些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变化。现在,我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毛泽东是始终站在被压迫者立场上,向现成等级秩序发起猛烈宣战的战士和诲人不倦的导师,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对另外一些身处精英或特权阶层的人来说,他则是一个也许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
蒂洛用那双透明的蓝眼睛盯着我,沉思了好一会儿,似乎想探明我说这番话的诚实性。半晌,他说:“我接触过中国不少知识界人士,他们似乎都不大喜欢毛主席,你是一个例外。”
“大概因为我没挨过整吧!”我开了个玩笑,“或者你想说,我是个反潮流的人?”蒂洛起先对我用了一个毛泽东时代流行的词汇一愣,接着也会心笑了起来。
在一次陪同蒂洛游览武汉大学校园时,我问起他对中国的印象。我知道他曾经好几次来过中国,先后在西安外国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过汉语,走过包括北京、西安、桂林和三峡等在内的不少地方,对中国社会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认识和感受。
“变化太大了。”蒂洛咕哝道,“几乎每次来中国,我都会发现一些新的变化。七八年前在西安,街头的外国人还寥寥无几,但最近一次去西安,我发现到处都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表情有点夸张,动作幅度很大地做着手势,“至于上海的变化就更让人吃惊,那些高楼大厦仿佛是一夜间长出来的,比东京和巴黎还要多。尤其是遍布街头的各种巨型英文广告牌,让你简直就象置身在纽约的曼哈顿一样,与之相比,德国的柏林和汉堡也显得黯然失色了。”
说到这儿,蒂洛似乎有点儿困惑。他说他也到过中国的内地和一些偏远乡村,那儿的落后和贫困同这些发达地区比较,简直就像隔着整整一个世纪。而这种差距和悬殊,大概只有在非洲的一些国家才能见到。“这真让人不可思议。”他不无惶惑地说。
但更令蒂洛觉得难以理解的是,在他接触的中国人当中,无论是政府官员、知识人士,还是一般的年轻人,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采取一种不加任何选择顶礼膜拜的态度。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使本国人民完全忽略和抛弃了自己的思想传统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个性,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某种统一制定的模式,这就太糟糕了!”他垂下脑袋,将整个脸埋在支成三脚架的胳膊上,皱着眉头,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
过了片刻,蒂洛抬起头来,神情忧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了几岁,像一个18和19世纪的欧洲浪漫诗人,比如拜伦。他还对我讲起去非洲的一些见闻,那儿难以想象的贫困、饥饿和没完没了的种族仇杀和政变。“这些灾难都是美国和欧洲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非洲实行殖民化和掠夺带来的。现在布什他们还在这样干……”
蒂洛显得很激动,甚至愤慨。酒吧内光线暗淡,但我还是能够看见他的额头冒出了一层亮晶晶的汗珠。他仰起细长的脖子,喝了一大口冰镇的西瓜汁。
我默默地倾听着蒂洛的讲述,没有吭声。我能说什么呢?或许我不能完全同意蒂洛对中国走马看花得出的印象,但我至少应该保持尊重吧。我想到现今中国跟蒂洛同龄的那些时尚青年和小资白领们,他们如果听了蒂洛的这番话会做何反应?吃惊?反感?不屑一顾、反唇相讥?甚至骂一句“站着说话不腰疼”扬长而去?不得而知。不过,此时此刻的蒂洛,却分明使我看到了那位没见过面的老迪芬巴赫先生的影子。
为了摆脱这种过于严肃乃至有些压抑的气氛,我把话题转向了文学,德国的,中国的。我提到了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以及伟大的歌德, 当然,还有本雅明。但蒂洛对讨论自己国家的文学似乎没什么兴趣,而更愿意谈论中国的文学。哦,我差点儿忘了他是个汉学博士,还出版过一本专著《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暴力倾向》。我向蒂洛了解几位中国当代作家在德国的影响和译介情况,据国内媒体的介绍,他们在美国、法国和日本介绍得比较多,我想蒂洛应该比较熟悉。可出乎我意料的是,蒂洛的反应有点儿冷淡。
“我很少读翻译过去的中国作品。尽管比较费劲,但平时我总是尽量读原文的。“蒂洛说,“您提到的这几位作家,有的我知道,读过他们的小说,觉得很容易从中看到某些西方作家的影子,好像他们总是在跟着西方的文学潮流跑。就我个人的兴趣,我还是喜欢从文学作品里感受到一个国家、民族和时代的社会状况、人的个性和真实的生活,他们的痛苦、焦虑和希望,等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比现在流行的那些东西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刘先生,难道你不这样认为么?”
蒂洛再次让我感到了意外。但我避开了他有点咄咄逼人的反问,我只是说:“在中国文学界,马克思可是早就有些过时啦……”
“不,卡尔.马克思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蒂洛用认真的口吻说。他甚至在空中使劲劈了一下右手。
我想,这真是一个不断让人吃惊的蒂洛。
剩下的一天时间,我没有陪同蒂洛。他拿着一份武汉交通图,自己去逛街了。单枪匹马,自由行动,这是大多数外国人的习惯。
晚上碰面时,我问他对武汉的印象如何。
“挺好,挺好!”他连连点头。
“是吗?”我有点儿怀疑地瞅着他,“在许多上海人眼里,武汉也许只不过是座大县城呢。”
“可这座城市的个性很鲜明,至少不像上海那么‘殖民化’。”蒂洛仍然坚持说,“只不过实在太热了!”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津津乐道地谈起自己的街头见闻。他说他在电信局给刚满两周岁的小侄女打了电话,小侄女大概刚睡醒过来,迷迷糊糊,一直没弄清楚自己是在跟谁说话。他想买一本王充的《论衡》,但跑了好几家书店也没有买到。他年底还要来一趟中国,要在北京大学作一场关于王充哲学思想的学术报告。“不过没关系,回上海后我再去书店找。”他说。
晚上,我们在前一天坐过的那家小酒吧喝了一点冷饮,吃了两份煲仔饭。蒂洛的心情不错,给我聊起他的恋爱经历。他说他曾经谈过几个女友,一个是日本的,一个是捷克的,还有中国的,都没有成功。他特别提到北京的那场“恋爱”,他们谈了大半年,死去活来的,但后来却发现女友原来已经结过婚了,有一天,那位丈夫找上门来,对他挥舞着拳头大吼大叫。两人干了一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蒂洛念出一句毛主席语录,并捋起袖子,对我露出胳膊上一块显眼的伤疤来,活像北京的那种“愣头青”。蒂洛还兴致很浓地唱了几首中国的流行歌曲,包括《我爱北京天安门》,他摇晃着脑袋,连唱带表演的,嘴巴还一边模仿电吉他伴奏,一脸可爱劲儿,惹得酒吧的服务小姐都忍不住笑了。
结账时,蒂洛拦住我,执意要付钱。“刘先生,你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他用恳求的语气说。
在陪蒂洛回旅馆的途中,他突然提出要去附近的一家乐器店看看。他说他想买一把吉他。
在小乐器店,蒂洛一进门就盯住了挂在墙上的几把吉他,并且取下来,一把一把地试音调弦,忙得不亦乐乎,像个十足的行家里手。
此时的蒂洛,显然已经不再是那个总是出语惊人的汉学博士,而变成一个如痴如醉的吉他乐手了。
当然,蒂洛最终一把吉他也没选中,他在女老板遗憾的目光注视下,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乐器店。
第二天,蒂洛就离开武汉了。他还要在上海逗留一段时间,然后从那儿回德国。
蒂洛回到德国后,通过电子邮件和我经常保持着联系,大多是谈对我作品的阅读感受,以及关于他那个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
12月初,蒂洛果然又到了中国,在北大做关于王充的学术报告。他在邮件里说,这个报告对他很重要,他为此作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如果成功,他可能要在北大担任一年的访问学者。“这样,我就可以更加有条件对中国文学展开深入的研究了。”
本来,蒂洛还想邀我去北京会面,受邀的还有张炜、刘庆邦先生,蒂洛曾经译介过他们两位的作品。但我因家事没有成行。
现在,蒂洛在北大的讲学想必结束,早已回到德国了吧?
2005/1/17 武昌
【读者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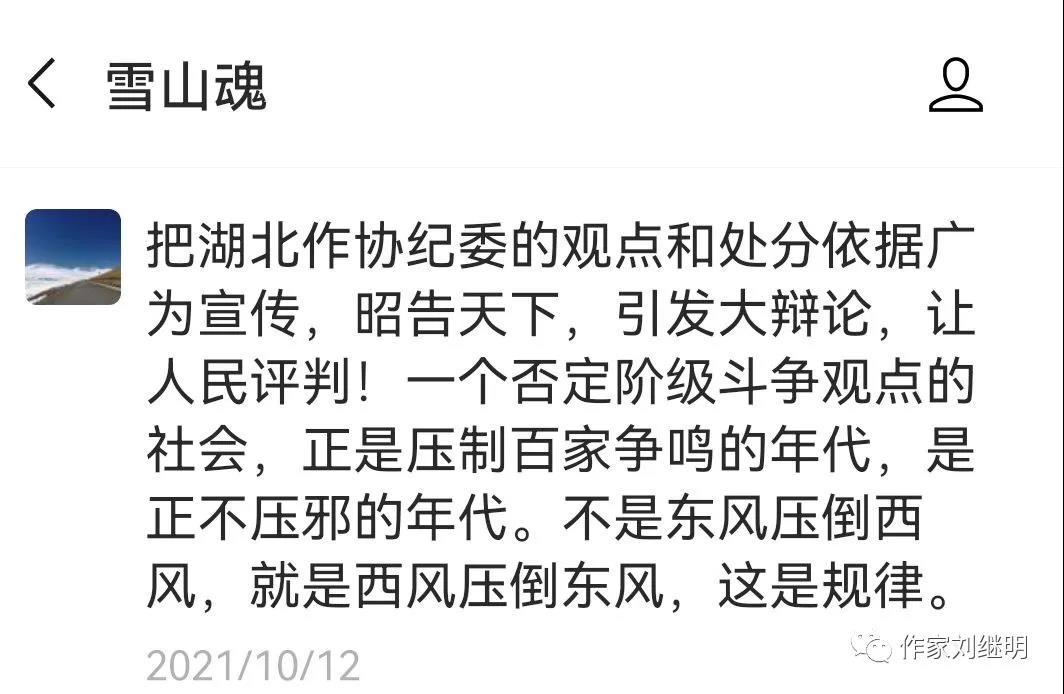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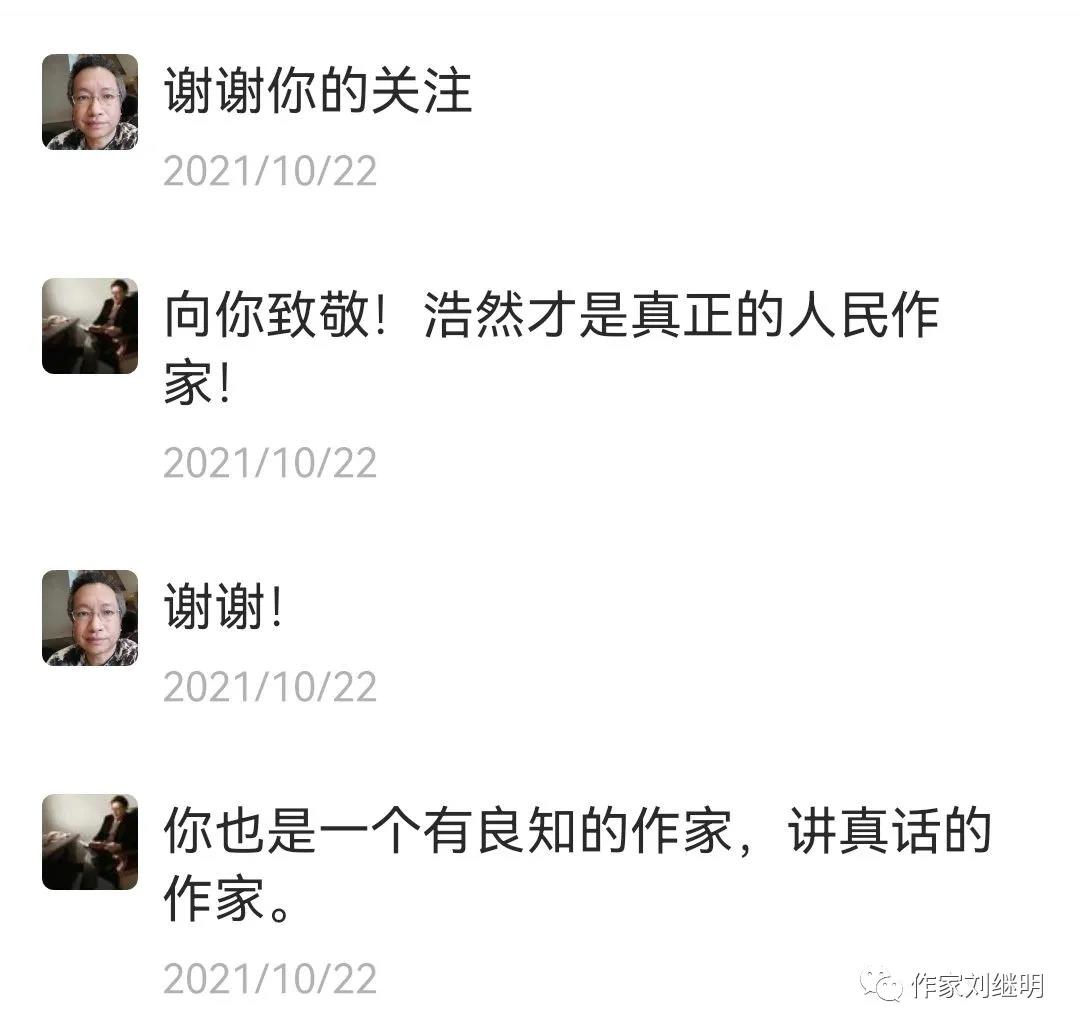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