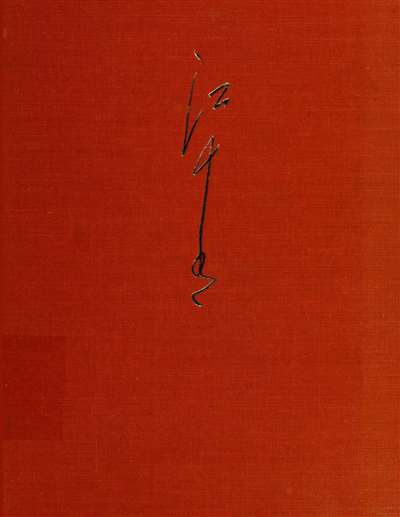
私以为,传记应当突出被记录人的事迹和思想,而非掺杂个人私见。写传记时,如果带入作者的私心杂念,往往会偏离主题,最终的作品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这本书,虽然从书名上看似是为李进同志而写,但实际上却借李进同志失势之机,转而对她进行污蔑。书名《李进同志》表面上是赞扬,实则是贬低。作者并未站在被记录人的立场,而是从资本主义圣母的角度进行书写,为修正主义者辩护,为自由主义者呼喊。
李进同志的本意很单纯,她希望作者能像埃德加·斯诺那样,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大背景下,写一部关于她革命事迹的传记。她每一句话都有录音,作者的任务仅是将这些录音整理成一本可供阅读的书籍。然而,现实却背道而驰,完全偏离了预期。李进同志万万没有料到,维特克女士并未像斯诺一样,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站在她的角度进行书写,而是从资产阶级的视角着手,写了一本充满阶级妥协和圣母式情怀的传记。书中不仅将李进同志描绘成恶俗的女权主义者,还为坚持文艺路线自由主义思潮的“四条汉子”辩护,为XXX、XXX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者歌功颂德。
对于普通人来说,翻译这样一本书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没有专业工具,单凭个人努力,一两年内也难以完成。幸运的是,我们如今能够借助AI工具。因此,这本中文译本是我借助AI完成的。尽管语言上可能不够自然流畅,尽管原文充满了作者的主观偏见,我还是尽力借助AI,尽量按照李进同志的立场,或更准确地说,按照马列主义的立场,修正了作者的一些反动观点。对于无法改正的部分,比如序言以及最后一章中的污蔑性内容,我已经一一删除。此举是为了让读者了解真相,因为我这里只想展现李进同志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对于伟大的革命家,我的眼中容不下任何污点,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颠倒的历史再次颠倒过来。
在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审视与反思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浮现出来:有时,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观察者反而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一些根深蒂固、却被身处其中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被揭示,便可能成为攻击无产阶级政权的有力工具。其中,最突出也最隐蔽的,或许并非通常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更为古老和顽固的幽灵——封建主义的法权,其核心表现即是森严的等级制度。
尽管文化革命旨在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旧有的官僚等级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主观意愿上普遍反对经济特权,但某些深植于文化与制度中的特权现象依然存在。这些现象,因其与革命功勋和特定历史人物的绑定,而被默许甚至合理化。例如,李进同志能够动用其影响力为外国友人维克特女士安排专场戏剧演出、调动专机直飞广州,并拥有个人的疗养别墅。
对于为新中国诞生付出巨大牺牲的开国元勋而言,这些在当时看似细微的特权或许情有可原。然而,这引出了一个更为棘手且无法回避的问题:这种基于身份和地位的“法权”是否具有可继承性?革命元勋的后代,是否能够理所当然地承袭其父辈的特殊地位与权益?这个问题如同一道幽灵,困扰了中国社会数十年,至今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历史的演进似乎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当第二代领导集体登上历史舞台后,这种源自等级的法权非但没有受到系统性的限制,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表现不仅在于经济领域的特殊利益固化,更在于上层建筑中官僚等级制的全面泛滥与精致化。这种从“革命元勋的应得待遇”到“官僚体系的固有权利”的演变,难道不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在此之前,社会主义苏联的蜕变就已经提供了一个冰冷的前车之鉴。苏联的变质看似是赫鲁晓夫一人捅破的窗户纸,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官方就过早地宣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消灭,这似乎让他们忘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反复警示:小生产者每时每刻都在自发地、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
在国家机器内部,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集团正是这种“再生”过程最集中的体现。以“物质刺激”为核心的激励政策、为高级干部服务的特供商店、以及固化的干部等级待遇,都为特权阶层的迅速形成与壮大提供了温床。苏联的悲剧恰恰在于,这个新兴的官僚特权阶层最终窃取了国家权力,将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工具。内部矛盾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仅仅是揭开了盖子,使长期的量变最终引发了质变。
最初,人们或许寄希望于通过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和提升领导干部的个人思想觉悟来限制特权的滋生。然而,这个教训深刻地揭示了:仅仅依靠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或思想觉悟,又或者是人民监督,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对抗体制性腐化的。必须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能够从根本上破除特权土壤的制度。而这一制度变革的核心,必然指向一个敏感的领域:打破官僚体制。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大一统”是根深蒂固的政治理想,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辽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追求。然而,这种观念很少从权力的另一面被审视:理想的情况是,国家的疆域越广阔,治理的链条就越长,中央统治者进行有效管理的难度就越大。对于现实中的统治者而言,广阔的疆域意味着“皇恩浩荡”,可以调动的资源更多,其统治集团的利益也相应越大。与此同时,这个权力核心也将变得愈发隐蔽和神秘,逐渐脱离基层人民群众的视野与监督。俗语“山高皇帝远”,不仅精准地描述了中央权力在传导过程中的衰减和扭曲,也从反面说明了地方人民对最高统治者监督的缺失。其结果必然是,中央权力集团愈发容易肆意妄为,而地方人民则愈发可能遭受层层加码的横征暴敛。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何跳出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周期率,是毛主席作为最高领导人,尤其是在其晚年,持续思考和探索的核心命题。他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并非简单的个人腐化,而在于一种能够自我再生、不断固化的“法权”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脱离人民的官僚阶层。面对这一根本性挑战,他提出的一系列看似零散的构想与社会实践,若将其串联起来,便共同指向了一个颠覆中国数千年政治传统的宏大目标:解构高度集权的中央“利维坦”,构建一个权力分散、基层自治、中央与地方呈“松耦合”状态的新型国家形态。这一构想的碎片,散落在他晚年的各项决策与指示之中,共同构成了一幅旨在从根本上瓦解官僚体制及其固有法权属性的蓝图。
传统国家理论中,权力的顶峰必然指向一个唯一的、拥有最高权威统治集团,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越往顶层,权力越大。毛主席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取消国家主席:这并非一时兴起或单纯的权力斗争策略,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制度性思考。通过在宪法层面取消国家元首这一职位,意在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权力的“人格化”象征,避免权力因过度集中于一人而带来的巨大风险和个人崇拜的制度化。中央权力的“虚化”与下放:他极力推动中央权力向地方转移,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在这种“松耦合”(Loosely-coupled)体制中,中央的角色不再是事无巨细、无所不包的“超级管理者”,而转变为宏观战略的“领航员”。中央的核心职能是制定关乎国家根本走向的大政方针,提供指导性的、而非指令性的粗略计划。具体的执行、管理和因地制宜的创新,则交由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地方政权去完成。
权力的下放若无相应的基层组织承接,只会造成混乱。因此,对基层政权的彻底重构是这一构想的基石。文化革命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本质上是一场旨在打破传统官僚科层制的颠覆性实验。并借鉴“鞍钢宪法”模式——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农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农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创造出一个能够防止任何单一群体(尤其是专业官僚)垄断权力的权力结构。与“革命委员会”相配套的,是推行更为广泛的直接民主与选举制度。其核心理念是,权力的合法性不应仅仅来源于上级的任命,而必须植根于基层民众的直接授权与持续监督。这从根本上挑战了延续千年的“官治”传统,试图转向真正的“民治”。建立民兵制度,逐步取代常备军以及警察部队等暴力机关,民兵制度,即“全民皆兵”,其战略意图远不止于应对外敌入侵。在对内层面,一个高度组织化、普遍武装化的民兵体系,逐步用全民武装性质的民兵,来取代耗资巨大、且容易成为“国中之国”的职业化常备军。当保卫国家的责任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时,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作为统治工具的特殊暴力集团便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无疑是整个国家学说中最为激进、也最为深刻的一环。
任何上层建筑的变革都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早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就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不能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应在广阔的内陆地区大力发展工业,以改变旧中国留下的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其直接动因看似是为了应对苏联可能发动的核打击,建立一个稳固的战略后方。但从更深远的层面看,这或许正是毛主席顺水推舟,利用外部压力来推进其内部战略构想的绝佳契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帝国”的核讹诈,要在和平时期推动如此大规模的资源从沿海向内陆转移,其阻力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三线建设”的战略意图远比单纯的国防考量要复杂。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更重要的是,它为那个设想中的、去中心化的“松耦合”政治体制,提供了一个分散化、网络化的经济基础。当经济不再过度依赖少数几个沿海中心城市时,地方的自主性和与中央的博弈能力自然会得到增强。
但是,历史永远都不可能是径情直遂的,总是充满艰辛和曲折得到,在毛主席逝世后,就像法国大革命的反复胜利和失败一样,有些人堂而皇之地把法权无限扩大,再次把松耦合的中央体制,变成中央集权制,逐步使社会主义退化成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完全消灭官僚阶级,革命造反派领袖和官僚特权阶级的关系只是建立在一个极不稳定的表面和平共处实际充满危机的平衡上的,就像李进同志在1974年所处的环境政治一样,造反派与官僚阶级表面上虽然和平共处,实则暗藏杀机,虽然造反派掌握着批判的武器,但是武器的批判却掌握在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虽然毛主席一直维系着这个平衡,但是当支持造反派的领袖去世后,胜利的天平自然而然地倒向了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官僚阶级一边。所以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官僚体制上,与其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如杜绝使一国事务集中掌握在某一官僚群体手里。因为这个群体始终是代表特权阶层,即使是坚持让特权阶层每年抽三到四个月去工厂或田间劳作,即使可能在精神层面上克制自己的法权,也无法改变特权阶级的固有属性。
虽然历史最终没有沿着这条理想的路线走下去,难道就意味着那场深刻的社会实验毫无价值?不!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十年里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即使社会主义已经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新生事物也是无法毁灭的,因为它们是革命的,是不可战胜的,经历过风吹雨打的它们反而会越来越茁壮地成长。虽然这些实践在那个时代受限于落后的生产力、低效的信息传递手段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群众的直接民主往往因信息不对称而陷入混乱,去中心化的管理也常常因为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而导致效率低下。然而,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初的实践瓶颈,正在被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革命所逐一攻克。人工智能(AI)的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实现“去领导人化”的分布式治理提供了技术基座。这不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我们每个人手中的智能手机,正在演变为一个强大的个人决策终端。在这种模式下,传统的“领导人”角色将被极大地削弱,甚至被“共识算法”和“集体智能”所取代。他们的职能,将从拥有最终裁决权的“统治者”,转变为服务于公共议事平台的“协调者”或“执行者”。国家治理将不再是少数政治精英在密室中进行的权力游戏,而将成为数十亿人民通过个人终端共同参与的开放进程。这正是那颗在半个世纪前被播下的“新生事物”的种子,在信息时代的土壤中找到的全新生长方式。
前一天还因为这些法权而绝望,然而半夜的清醒使我信心百倍,写下此文,一为译者序,二为破除法权(特权等级)滋生抛砖引玉。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