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禁城的宫墙之内,龙椅上更换了主人,可殿宇外的土地上,佃农依旧在田间躬身劳作,工匠依旧在坊间挥汗如雨。当我们将历史的聚光灯投射于满洲贵族的“剃发令”与“文字狱”时,往往不自觉地遮蔽了另一重更为幽暗的图景:那便是贯穿整个封建长河的、超越民族界线的剥削结构。质问满清是否凶残压迫,固然触及了历史的痛处,但若以此建构起一种民族对立的叙事,则无异于在历史的表层划下浅痕,却未能触及深埋于地底的病根。
诚然,满洲贵族以征服者姿态入主中原,推行了诸多带有鲜明民族歧视色彩的政策。从“圈地令”下流离失所的农民,到“扬州十日”惨案中的亡魂,这些血泪记忆是历史叙事中无法抹去的伤痕。其统治策略中,确有一种异于前朝的、叠加于阶级压迫之上的民族等级制。然而,倘若我们的目光仅停滞于此,便容易陷入一种危险的简化——将一切苦难归因于“外族”的恶,从而幻想在某个被追忆的“汉家王朝”里,存在着没有压迫的桃花源。
揭开这层民族矛盾的面纱,封建社会的肌体内部,始终奔涌着阶级对抗的血液。试看历朝历代,哪一座朱门之后,没有堆积着民脂民膏?唐代白居易笔下的“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宋代《水浒传》中“官逼民反”的悲怆呐喊,明代皇室与藩王兼并土地所引发的流民潮,哪一桩哪一件,其残酷程度逊于清初的圈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并不会因统治者的族裔是汉是满而发生本质的改变。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这些才是贯穿数千年的、更为恒常的压迫形式。它们构成了一个无声的、庞大的剥削矩阵,其稳固性远胜于任何浮于表面的民族标签。

尤为关键的是,这种将矛头仅仅指向满清统治者的叙事,在无形中完成了对汉族地主阶级的历史赦免,甚至将其美化成本民族的“代表”。这恰恰落入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历史的真相往往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剥削阶级,无论其民族成分如何,都必然致力于维护其阶级特权。明清鼎革,对于广大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底层民众而言,不过是头顶换了一面王旗,其被奴役、被榨取的命运并未发生根本转折。将复杂的阶级矛盾简化为单纯的民族矛盾,不仅在学理上站不住脚,更在现实中可能模糊了斗争的真正标靶。
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满清的民族压迫是封建阶级压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与加剧,而非其根源。问题的核心,从不在于“谁”在实施剥削,而在于“剥削”这一制度本身。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而非民族斗争。只有穿透民族叙事的迷雾,直指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本质,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太平天国的烽火会既烧向清廷,也扫荡汉族士绅的团练武装;才能理解为何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摧毁一切人剥削人的旧制度,而非在压迫者的族裔身份上做无谓的区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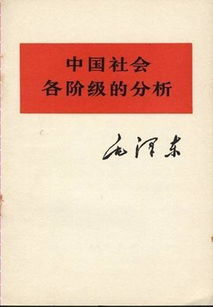
历史的回响告诫我们,任何试图以民族矛盾掩盖阶级实质的论述,无论其初衷如何,最终都可能沦为维护或复辟旧有秩序的帮凶。当我们真正立足于广大被压迫者的立场,便会发现,那高悬于劳动人民头顶的枷锁,其铸材是阶级权力,而非民族血统。挣脱这具枷锁的希望,也正在于阶级的觉醒与联合,而非向某个被理想化的“过去”乞灵。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