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难得会公开承认自己害怕自由。相反,他们往往把自己扮演成自由的捍卫者,以此来掩饰(有时是无意识地)内心对自由的恐惧。作为‘合适的’捍卫自由的人,他们....常把自由与维持现状混为一谈,以致于一旦意识到有可能认清所说的现状,意识就因此似乎会对自由本身构成威胁。’
——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
刘道玉死去了——像以往一样,神圣的,伟大的,‘自由的’八十年代又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人们复读着那些早已被我们熟悉的陈词滥调:真正的独立人格,真正的独立思想,‘激进的’改革者,先驱,前卫的象征...坦言之,在连这样一点可怜的自由都已经不可能再被容忍的时候,怀念它是一件多么自然的事情。

但是,如果抛开那种纯粹的,对于某种记忆里的,令人眩晕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怀念,刘道玉的真实遗产是什么?他的‘激进改革’,究竟是向我们指明了一条解放之路,还是说,不过是另一个幻影,一个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暂且让幻想栖身的处所。

80年代的文化热潮被想象为‘启蒙’的黄金岁月
教育自由还是交换自由?
刘道玉所留下的最大遗产,无疑是在培养方案上的灵活机动。学分制,双学位,专业之间的灵活转入与转出...作为对‘机械的’‘僵硬死板’的‘苏式教育’的反叛,它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改革的目的究竟是要废除教育当中的实用主义,还是从官僚主导的。行政国家的实用主义,转变成一种个人的实用主义?在《自白》当中,刘道玉明确写道,实施上述改革的重要考量在于:‘在实际工作当中,某些专业培养的学生明显是没有出路的,要么分配不出去,要么出去了也要改行,存在着学与用的尖锐矛盾:数学,理论物理,俄语,法语,哲学,历史...都有这个毛病’,为此,‘最好要实行双学位制’,让学生在一个专业以外,还有‘另一个饭碗’以‘拓宽就业’——最后,数学要与经济、管理、统计学等专业关联,历史学要与新闻、行政管理关联,哲学则要与经济系、社会学等关联。
一言以蔽之,在教育自由的背后,并不是求知自由,真理自由,而是市场自由,交换自由。是要让大学教育为就业直接服务,把大学教育改革的指挥棒,交到市场的热门行业手中。刘道玉夸耀说,‘经过这一改革,涌现了大批横向成才的先进典型:学历史的,有很多成为了报业的领导人;学哲学的,有很多最终成为了企业家;学数学的,则去当了经济学家和银行的高级雇员....’但是,回到历史学,哲学和数学这些基础学科本身的发展究竟如何的问题,刘道玉就再也未着一词了。在晚年,刘道玉不止一次地批判大学的浮躁之风,然而这种浮躁本身,岂不是也有他在市场化大潮之下‘顺势而为’的一番贡献吗?在‘走出为国家眼前的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思维’(2012)之后,走向的不是刘道玉宣称的人类的终极追求,而是‘为自己捞取经济利益的现代思维’。
精英领导反对教育无政府主义
刘道玉一向是某种精英教育的拥护者(《论古代书院教育模式的复兴》,2019)——实行通识教育的目的虽然在于‘全人’,但是这种全人却注定是极少数顶尖的‘领导者’的品质,正如古典贵族的自由七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2010)的采访时,刘道玉直言不讳地说到,‘一流大学’就是能够培养‘一流领袖的大学’,就是培养‘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领袖’的大学,就是社会的统治者的大学。‘我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些专门培养精英的大学。前几天李政道在北师大有个演讲,他说培养创新人才就是要进行精英教育,要一对一教学。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就是一对一教出来的。这就是精英大学。’对应地,‘大家都要当一流大学,这就是不可能的’——在大学教育当中,正如在社会生活中一样,应当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是少数精英和多数愚人的差别。
刘道玉对‘极端民主派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是一贯的(参见《自白》第97-99页):‘过去我们搞什么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是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的进行的,什么精神也都是自上而下的,先党内后党外进行传达。只有这次CR不同,什么事情都是一竿子到底,群众知道了党还不知道。’这在教育问题上也不例外:他无法通过群众和社会的角度思考自我教育,而始终只能够是基于社会金字塔的,教育者的教育。‘作为压迫者阶级,他们都无法与人民一道进行思维,也不允许人民自己为自己思维。’(《被压迫者教育学》CH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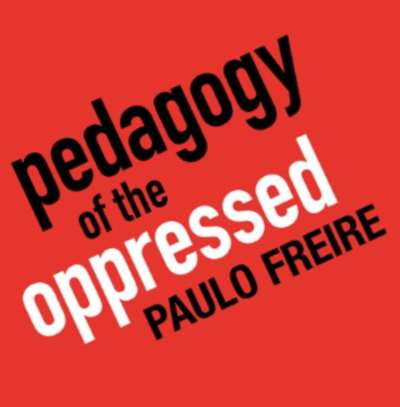
固然,刘道玉反对官僚团体的行政领导。‘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目前的这些示范学校,都是依靠教育行政部门才树立起来的,是依靠人为配备优质教育资源而出名的,并不是通过平等的自由竞争而产生的。所以他们不仅起不到改革示范的作用,而且是应试教育的活样板’(《论爱的教育》)。然而,依靠‘平等的自由竞争’,并不见得会做的比‘人为地配置资源’更加公平:当东部沿海或省会城市以重金聘请中西部地区的优秀教师,网罗优质生源并造成教育资源的外流和‘县中’的不断衰落时,这究竟又在何种程度上保障了教育公平?在残酷的市场厮杀当中胜出的‘名校’,其优越性与那些官僚团体打造的样板间相比,又在何种意义上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可以确信,刘道玉校长的改革将诞生出更多的精英,可惜我们并不是精英集团的候选人,为此也不关心它的未来发展。
独立而无批判性的思想
刘道玉提倡反思精神与独立思想:‘“独上高楼”是什么意思?就是进入“象牙塔”,像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说:“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从事高深学问之研究。当今,我们的大学做不出传承千百年的学术成就,就是缺少了这种精神。’(《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2012)。但是,刘道玉所说的‘独立’,无非是与某一个特定的规章独立,与某一套体制独立,与某一个上级独立,但是却从不是一种从自身出发的反思精神。刘道玉既是一位体制的‘弃儿’,也是一位时代的弄潮儿。就此而言,他并没有领悟到韦伯所说的‘学术作为志业(天职)’的真正意涵。在刘道玉身上,聪明的计算(Berechnung)从未离开,不过是失之于东,取之于西,失之于政坛,取之于市场。而在韦伯的设想当中,学术自身乃是一种在理知化的时代自我坚守的天职,它尤其需要对抗现代性(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侵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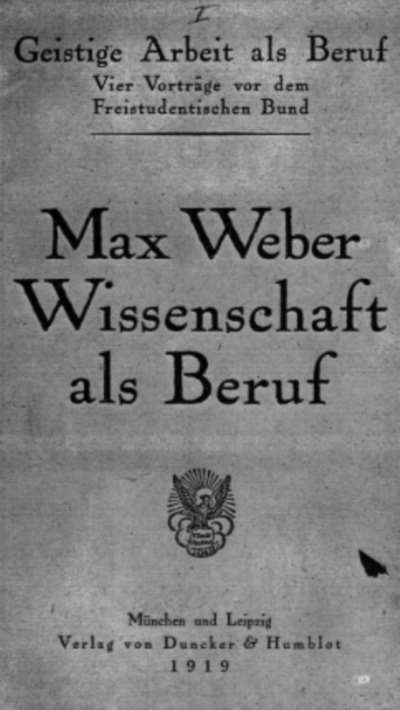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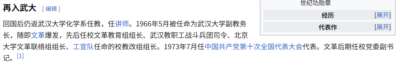
在刘道玉的独立思想当中缺乏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真正深切的反思,反而随处可见对既有的分化与分工的接受——这正是他的‘象牙塔’追求所致。正是因为将自己仅仅定位为象牙塔中的一份子,并且十分满足于这一身份,刘道玉的独立思想不仅不独立于压迫性的社会结构,而且是在时时刻刻地维护着它。刘道玉没有看到,大学校长不可能一方面将自己理解为‘纯粹的职业教育家’,另一方面还‘比一般的知识分子更有担当’,‘能批评政府,呵斥腐败,声援弱势群体’(接受东方早报的采访,2011)。十分讽刺地是,刘道玉对着《东方早报》的记者大谈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当中的知识分子理想,却并未注意到这本演讲集的根本旨趣就在于反对知识分子的专家性并倡导其公共性。
从根本上说,刘道玉的独立性暗示着知识精英的一个特殊性地位,建立在有知者对无知者的权威之上。刘道玉并不打算否定并打碎这种权威。他攻击的是‘无知者’(党务官僚)名不副实的权威,而试图用有知者名实相符的权威来取代它。就此而言,他的独立在根本上是非批判的,是对于社会秩序,分化以及等级制特征的全面接受。
结论:并不激进的‘激进教育家’
将刘道玉视为这个国家的‘激进教育家’是一种时代的滑稽。在刘道玉的教育思想当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的平民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要素,没有发现他与人民进行平等的交谈,进而促进他们去推动自身与社会变革的任何企图。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始终处在权力漩涡中央的‘不倒翁’作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自鸣得意:谈论对于人性和意志的尊重,却不谈论如何去帮助人们发现他们自己的人性和意志,好像他们已经不是奴隶,已经可以为自己做主了一样。对于被压迫者而言,正如弗莱雷所言,后者才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困难的——他们还根本就不具有‘自身意识’,还没有明白自己是谁(《被压迫者教育学》CH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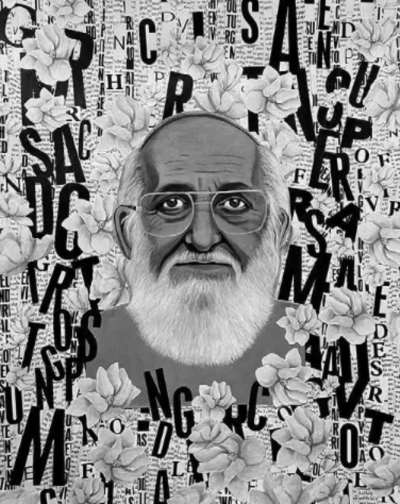
在《无知的教师》的中译本序言一开篇,朗西埃曾经指出,在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同样出现过‘教育改革’的热潮——而这一热潮的目的就是‘完结革命’:‘终结革命所引起的反复动荡和种种热望,转变各种机构和人们的心态,进而来扼制革命的暴力;走出狂热迫求平等的年代,为社会和政府构建一种新的现代秩序,以此沟通进步与秩序(稳定)’。朗西埃强调 ,教育在这一新秩序的建构与巩固当中发挥着枢纽性的作用:它一方面确认着基于所谓‘智识差异’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地教育‘提升’过程而制造一种不断‘平等化’的假象——教育过程标示出多数人‘进步’或‘上升’的‘能力极限’,同时把少数人擢升为新的‘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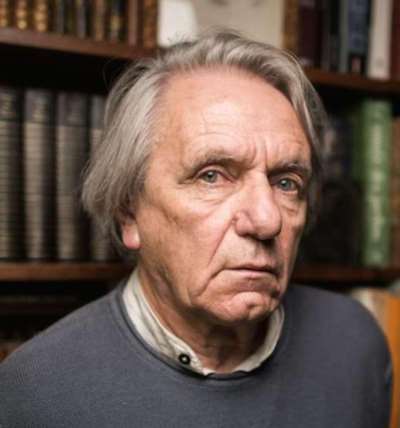
刘道玉是这一传统在我们时代的继承者。一方面,他确认了教育本身的开放性与动态性:被教育者能够转化为教育者,无知者能够变得有知。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这种教育只能是基于等级秩序的,并且其目的不在于真正消解等级秩序,而在于不断地填补它所造成的裂隙,不断地在令人彻底绝望的断裂当中架起一道桥梁。他从不平等的现实出发,宣布将不断地修复它,并且在这种不平等的在生产当中修复新的不平等。
总而言之,作为教育学家的刘道玉所持有的始终是教育者的教育学,而不是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前者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大学校长,正如告诉我们如何成为好的精神病院院长与警察局长,而后者则告诉我们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被压迫者——自身的人性究竟何在,并且与我们自身一道前进。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