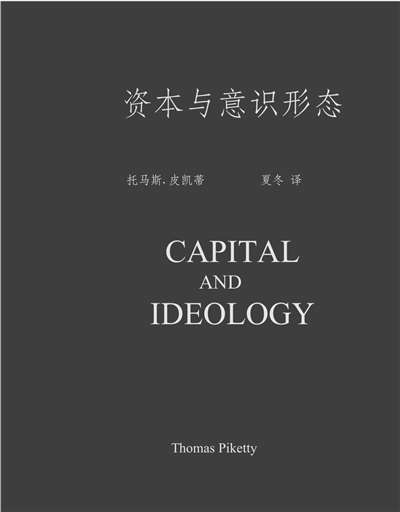
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对正义的追求
“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写道。他们的主张仍然中肯,但既然本书已经完成,我很想将其重新表述如下: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和追求正义的历史。换句话说,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历史中很重要。社会地位尽管很重要,但不足以形成公正社会理论、财产理论、边界理论、税收理论、教育理论、工资理论或民主理论。如果没有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明确回答,没有政治实验与社会学习的清晰战略,斗争便会在政治方向上陷入迷惘。一旦权力被夺取,这种真空往往会被新的、甚至比旧制度更为残酷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填补。
考虑到二十世纪的历史和共产主义幻灭,我们必须仔细审视当今的不平等制度及其合理性。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和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组织能够真正促进人类和社会的解放。不平等的历史不能被简化为人类的压迫者和平等的捍卫者之间的永恒冲突。双方都可以发现复杂的思想和制度结构。必须深入揭露、批判统治阶级虚伪、自私甚至反动的意识形态。不止单一化的“阶级斗争”,还要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意味着思想碰撞、经验交流、相互尊重、理性商议与真正的民主。没有人能掌握关于“正义的财产、正义的国界、正义的民主、正义的税收与教育”的绝对真理。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场永不停息的正义探索;唯有通过广泛的比较、历史经验的对照与最广阔的民主讨论,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对正义的追求也需要表达明确的立场和明确指定的对手。根据本书分析的经验,我坚信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是可以被取代的,一个公正的社会可以在参与性社会主义和社会联邦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第一步是建立社会化的和临时的公共所有权制度。这将需要工人和股东之间分享权力,并对任何一名股东可以投票的数量设定上限。这也要求实行高度累进的财产税、全民资本分配与财富的永久流通。同时,还需实行累进所得税与碳排放的集体调控,其收入用于社会保险、基本收入、生态转型与真正的教育平等。最后,全球经济需要通过共同发展条约进行重组,其中纳入社会、财政和环境正义的量化目标;贸易和金融流动自由化必须以实现这些主要目标的进展为条件。全球法律框架的重新定义将要求放弃一些现有条约,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效的有关资本自由流通的条约,因为这些条约阻碍了上述目标的实现。这些条约需要被基于金融透明度、财政合作和跨国民主原则的新规则所取代。
其中一些结论可能看起来很激进。事实上,它们属于一场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运动,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一直致力于法律、社会和财政体系的深刻变革。二十世纪中叶发生的不平等现象的显著减少是通过建立一个基于相对教育平等的社会国家和一些激进的创新(例如日耳曼和北欧国家的共同管理以及美国和英国的累进税制)而得以实现的。20世纪80年代共产主义的幻灭和保守派的复辟中断了这一进程;世界陷入“市场自我调节”与财产“神圣化”的新纪元。社会民主主义联盟未能突破民族国家的局限,也未能在全球化与高等教育扩展的条件下更新自身的纲领,导致战后得以削减不平等的左右翼政治格局全面崩溃。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放任资本主义的局限,随着不平等的重新恶化、全球化的危机与身份政治的退却,人们重新开始思考新的、更平等、更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我在这里提出的“参与式社会主义”与“社会联邦主义”,正是汲取了世界各地不同实验的成果;我的贡献仅在于为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角。
本书所考察的不平等制度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结论: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型并非宿命,历史从未是单线发展的。权力格局的变化总是取决于短期事件逻辑与长期思想演变的交织。而在危机时刻,恰恰是那些长期积累的思想资源,决定了社会能否开辟新路。危险在于,国家可能继续回避根本变革,转而加剧“人人相争”的内卷式竞争,陷入新一轮财政与社会恶性竞逐。这种局面不仅会阻碍解放,反而会助长民族主义与身份政治的分裂冲突,而这一趋势在欧美、印度、巴西与中国已经昭然若揭。
论我们目光“去西方化”的局限性
在本书中,我试图改变我们看待不平等制度历史的方式。印度的例子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印度联邦是大规模民主联邦制的一个例子。不仅如此,它还展示了国家如何利用法律工具来克服古代种姓社会因与英国殖民势力的遭遇而变得更加僵化的严重不平等遗产。印度为处理这一遗产而开发的制度工具采取了配额和“保留”大学、公共就业和选举职位名额的形式:名额是为出生于历史上遭受歧视的弱势社会阶级的个人保留的。这一体系并没有解决印度的所有问题——远非如此。但这些经验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因为它们也正在应对巨大的教育不平等(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忽视),并且刚刚开始应对多重信仰主义(印度从十世纪以来就知道这一点)。更一般地说,我试图表明,要了解当今世界,研究不平等制度的悠久历史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欧洲私有制和殖民列强影响非欧洲三元社会发展的方式。这段漫长历史的痕迹在当代不平等的结构中依然清晰可见。除此之外,对过去复杂的不平等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正确看待当今的意识形态。人们看到,它们并不总是比它们之前的意识形态更明智,而且它们有一天也会被取代。
尽管我努力分散我们的视线,但我不得不说这本书仍然不平衡——比我之前的书稍微少一些,但总体上仍然很不平衡。法国大革命一再出现,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也不断被引用,远远超出了它们在人类整体中的实际分量。杰克·古迪在《历史的盗窃》中曾尖锐指出:即便是“善意”的社会科学家,也常常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不自觉地把许多发明与文化实践归功于欧洲与美国——无论是“宫廷之爱”、自由理念、亲情观念、核心家庭、人文主义还是民主制度。事实上,它们并非西方的专属创造。我在本书中试图避免这种偏见,但是我不确定我是否成功了。原因很简单:我的目光深深地受到我的文化根源、我的知识局限性的影响,尤其是我语言能力的严重弱点。本书的作者只能流利地阅读法语和英语,并且只熟悉有限的主要资料来源。然而,这项研究的范围涵盖得很广泛,也许过于广泛,我要为在这里发现的概略和浓缩之处向其他领域的专家们道歉。我在此向相关领域的专家致歉,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研究能补充甚至超越本书,尤其是在那些本书涉及甚少的地区与文明中,深入分析其独特的不平等制度。
毫无疑问,我的视野也深受个人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我自己的自觉。我可以回忆出家庭背景中所接触到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思想的多样性:我的两位祖母都遭受了他们这一代人所强加的父权模式的压迫。其中一位在她的中产生活中感到不快,并在1987年提前在巴黎去世。另一位在二战期间13岁时成了一名农场女仆,于2018年在安德尔-卢瓦尔省去世。我曾从其中一位曾祖母那里听到关于1914年之前法国的故事,当时这个国家正在策划对德国的复仇。生于1971年的我,从父母那里获得了成为独立成年人的自由。1989年求学时,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东欧“共产主义专政”的崩溃;1991年,又听到海湾战争的报道。当我回顾我从18岁以来对历史和经济的看法是如何演变的时候,我认为正是对历史的研究——我所发现的资料和所阅读的书籍——使我明显改变了我的观点(我最初比现在更加自由主义,更少社会主义)。直到2001年完成《二十世纪法国高收入群体》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二十世纪的不平等削减伴随着巨大的暴力与动荡。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让我关注全球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以及资本与积累的历史,这也成为《二十一世纪资本论》(2013)的核心主题。至于本书,则主要依赖新的资料——尤其是殖民史与选后调查——推动我提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视角来分析不平等制度。当然,这一重构也可能过于理性化,忽视了我个人经历的潜在影响。但无论如何,我至少努力通过引用史料与著作,让读者能够看清我的心路历程。
论社会科学的公民和政治作用
社会科学家无疑是幸运的。社会供养他们,让他们能够写书、挖掘资料、汇总档案与调查所得,而他们本应将成果回馈给真正的支持者——人民大众。然而,社会科学研究者往往沉溺于学科之争和地位竞争,虚耗精力。尽管如此,社会科学仍是公共辩论和民主对话不可或缺的武器。本书正是尝试展示:唯有依靠多种社会科学的方法与资料,我们才能在社会、经济、政治与思想多重维度上揭示“不平等制度”的历史逻辑。
我深信,当下民主的混乱与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经济学的“自我割裂”与“知识霸权”。经济学不仅把自己与其他社会科学分离开来,还在资本和国家机器的庇护下,力图垄断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权。这种固步自封虽然部分是由于经济领域复杂性的增加,但更关键的是,职业经济学家——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市场——反复沉迷于一种虚假的诱惑:声称自己掌握了独一无二的分析力与解释力,从而获得对社会话语的独占地位。实际上,这是一种话语掠夺,是知识领域的“圈地运动”。
事实却恰恰相反。要理解社会经济现象,必须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政治学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冲破资本话语制造的迷雾,真正推动认知与解放。这不仅适用于阶级不平等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更是揭示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普遍原则。本书的存在,离不开众多跨学科社会科学家的成果;我也相信,就像社会科学一样,文学和电影也能为我们的课题提供启发。
经济学知识霸权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迫使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自我放逐,将经济问题拱手交给经济学家独裁。而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从来都关涉所有社会科学,是权力结构的总汇。所有社会科学家都必须直面社会经济趋势,收集定量与历史数据,在必要时采用多元方法,并对这些数据的社会、历史与政治条件进行批判性解剖。遗憾的是,许多社会科学家对定量与统计资料的轻视,不仅助长了经济学的霸权化,也让它自身沦为资本服务的贫瘠学科。因此,所谓“经济学的中立性”不过是资本权力的遮羞布。社会科学若要不背叛民主,就必须揭露并瓦解这种知识霸权。本书的目的,正是要为此提供一点火种。
超越学术研究领域,经济学知识的自我封闭与自我神化同样严重荼毒了公民与政治生活。它鼓吹一种宿命论思维,制造出无力感与麻木感。尤其是记者与普通公民,往往对所谓“经济学家”的权威顶礼膜拜,尽管这种权威本身极其有限,却依然使他们在工资与利润、税收与债务、贸易与资本等重大议题上畏首畏尾,不敢开口。倘若人民如民主所言应是至高无上的,那么这些问题便不是可有可无的。其复杂性之高,将其完全交由一小撮精英阶层处理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恰恰相反。正因为它们如此复杂,只有基于理性、以及每个公民的过去历史和经验的广泛集体讨论才能推动解决这些问题的进展。最终,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人民重新掌握经济和历史知识的所有权。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我的具体结论并不重要,因为我的目的是开启辩论,而不是结束辩论。如果本书能够唤醒读者对新问题的兴趣,并以他们之前所未具备的知识启迪他们,那么我的目标就达到了。
(需要ebook的请联系原载公众号译者夏冬)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