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7小学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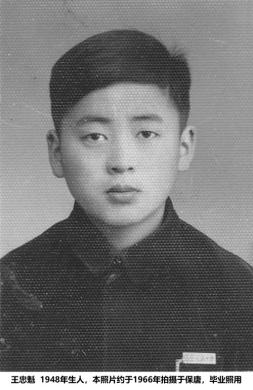
我的小学时代(二)
(1955年—1960年)[本章共10小节,分三次连载]
5.政治课与小剧团
在我所学过的课程中,中小学所学过的政治和高中时代所学过的三年的俄语是忘得最多的了,因为这两门课主要靠背去记忆的;而小学的政治课里,1958年那一段有些内容却一直在记忆里,这恐怕是在当时大力宣传和反复学的效果吧。
“高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方针”;“钢产量要达到1800万吨”等等很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我们当时大范围学唱的歌则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此外,还有“十五年内赶英超美”等歌。
政治课内容与歌不只是在学生中普及,公社还成立了很出色的小剧团。小剧团采用以“二人转”为主,“快板”为辅的宣传形式。当然,也演一些传统的节目,比如《铡美案》《白蛇传》等等。巴彦塔拉的小剧团是很有名的,武生、旦角都有硬手,吹打弹拉的鼓乐班子也都是解放前夕戏班子的成员。我敢说,这些人的水平绝不亚于今天赵本山《刘老根》的剧组成员。可惜,那时媒体不发达,无法大面积演出,除了少有的几台收音机没有别的。这些小剧团的人今天不是故去了就是人老珠黄了。我会哼哼“二人转”的各种曲调,也都是那两年常去小剧团在听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学会的。
宣传是为形势服务的,从上可以看到,随着“三面红旗”的诞生,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与此同时,“共产风”“卫星田”等事物也伴随着挤了进来。对于后者,今天的年轻人是想象不到的。
6.雨夜修河堤
1958年暑假,我们还没上五年级时,西拉木伦河[ 就是西辽河,辽河有两条大的支流,分别是东辽河和西辽河。其中西辽河发源于河北省北部,经内蒙赤峰地区时叫教来河,经内蒙通辽区域时叫西拉木伦河,东西辽河在辽宁省汇合后叫辽河。西拉木伦是蒙语,意思是黄色的江,它是中国的第八大河,在东北仅次于黑龙江,比松花江要大。]发了大水。有个阴雨天的午夜,老师带领几名学生把全班的男同学叫齐,拿上铁锹去大堤内修民堤。在几支手电筒的微弱灯光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站成一排前行着。路过柳条通[ 大堤至民堤间原来有许多柳树,建国后被砍掉了,但从树根处又发出来的密密的柳枝形成的灌木丛。]时,落豆秧[ 读烙豆秧,一种野生的匍匐生长的豆科植物,是牲畜们的上等口粮。]长的有一尺多深。我个子小,无论怎样抬高腿也很难迈出一步,队伍行动得很慢。好不容易走到了河边,见到社员们早已分段在猛干了。我们也在公社干部的指挥下分了一段干了起来。看不清河水,只隐隐约约见前边白亮亮的一片,河水呼呼地山响,太吓人了。
大同学干得还挺快,大家都像急疯了一样。而我,无论怎么急,每挖一锹土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好不容易挖下了一锹土,没等端起来就又被草根给拽掉在地上了,干着急不出活。老师很快发现了这种情况,同学们扔土都很难扔出,于是,叫大个子挖,小个子用手搬土……,我们的手上、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心情一个个紧绷绷的,一言不发,拼命地干,耳边只听河水的轰轰地响,如同催命一般的感觉。
天终于放亮了,一米多高的民堤也基本够高了。抬头一看,好家伙,民堤离河只有几十米远了,河水眼看就要出漕!真险啊!事后我们后怕地想,如果那晚河水出漕,人们跑得了吗?当然,我们觉得公社肯定指派了专人查看着河水,见事情不妙会提前叫我们撤退的。
那一年,河水终于出了漕,民堤也没能挡住河水。河水漫过民堤冲到了大堤[ 当地叫国堤,是日伪时期小鬼子组织当地人修的,建国后多次加固。是保卫巴彦塔拉的最后一道屏障。]一直上涨,几乎漫过大堤。护堤修堤的人们日夜拼命干,妇女老人[ 包括裹足的老年妇女。]编草袋。在全民的齐动员下,最后终于护住了大堤,家园保住了。
在夜修民堤的后几天,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们又参加了加固大堤上子堤的抢险劳动,女生也参加了。不过那是在白天。整个大堤上下都布满了人,心里没有那夜恐惧了。河水一来,野兔野鼠为了逃命,竟不顾大堤上的人群,拼命游上大堤被人们捉住。回忆起来,小学那夜的修民堤,是我一生中最惊险而恐怖的一件事了。我们提心吊胆地度过了那阴黑的几个小时,让我也了解到了河水发怒的威风。愿以后的孩子们不会再有我的经历。
1962年辽河涨水又出了一次漕,旗委书记[ 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叫法与其它地区不同。与地区相当的叫盟,与县相当的叫旗,与乡相当的叫苏木,与村相当的叫嘎查,这是蒙古语的称呼,表明该地区为蒙古族自治区,人口上蒙古族比较多。一般地,正职领导也是蒙古族。]亲自到中学动员我们初中生护堤抢险。堤外的高粱只露着穗子,而其他的庄稼则全完了。说也怪,越是涨水的时候,越是连雨天。但人们挑土奔跑着,只要在白天,修河堤的人并不惧怕,就怕夜里河堤漏水[ 也就是管涌,通常是因为堤上有老鼠洞或蚂蚁洞导致的。]。一旦有一小处漏水,大堤上有电话,指挥的人一讲地点,人们会跑去拼命堵,因此,从没出现因漏水冲坏大堤的情况,从这点看来我们比1998年的南方要幸运。
近几年,辽河很少涨水了,却连续多年干涸,这可能不是什么好事。河本是该有水的地方,怎么会连年干涸呢?人类对大自然的事情真该认真反思,全民动员来改变现状了。
7.种卫星田
不客气地讲,为了出政绩不切合实际的浮夸风把中国人折腾苦了。至今,仍有某些政客,要么是自己没吃过苦头,要么就是官位熏心,仍在欺上瞒下,走1958、1959年的老路。
大家都听说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相声里边的词吧?那时“亩产万斤”不知是从哪个地方吹起来的。我小学五年级在学校的安排下,班里也搞起了“卫星田”。
1958年我们那里本是个大丰收年,可惜忙于在上冻前大搞秋翻地大会战,地里的庄稼来不及收拾干净就干上了。当时有很多专门用来翻地的畜力双铧犁。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那根本来不及捡干净的大玉米棒子被翻扣在了地下面。甚至还有地头地脑来不及拉干净的豆铺子[ 割黄豆时为方便,会每隔两到三米把豆秧堆放成的堆。]。
你也许会问:“其他的人都干啥呢?”
人们都在披星戴月拿着铁锹翻地。机关团体停止上班,学校停课,凡能组织的人全动员起来了。每人一条垅,一排下去一两里路长,场面很壮观。那时比干劲,流传出的口号是“小孩赛罗成,老头赛黄忠,干部要赛诸葛亮,妇女要赛穆桂英”。
为了争取第二年大高产,上学后又大搞积肥捡粪活动,各年级的学生每天上学都要拾一筐肥送到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个大大的粪堆,还要比插红旗班。人多粪少,免不得起早贪黑地干,业余时间捡粪成了我们的主要活动了。当然,在比谁捡得多的同时,大学生们还刨一些灰土粪,两三筐顶一筐地往学校送。学校的十几个大粪堆起来了。
怎样夺高产呢?搞“卫星试验田”!
四年级往上的几个班每班分了一块约半亩的土地,快放寒假前,地冻三尺多了,开始深翻地。
何谓深翻?即要挖两米多宽、一米深的长长的大沟。挖好后一层粪一层土地填好几次把沟填平。然后在大沟的一侧紧挨着原沟再挖这样的沟。所谓挖,实际上是用镐一小块一小块地刨。每挖一筐土,就是好劳力也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没有十多分钟是刨不出一筐土来的。我在班里最小,才十岁半,举起镐都挺费劲的,好在任务是全班大协作,大龄学生中有几个十七八岁的,刨土的活主要是他们包了。我要干时他们当然也让我刨几下,原因是他们也要喘口气。至于我能刨下几块冻土,班里的大哥大姐们是从不责怪我的,因为我也尽了最大努力了。
有人会问:“你们干嘛不在秋翻地一结束,刚一上冻前就深翻呢?那不是会省很多力气吗?”
道理很简单:白天上课除外,晚上要常常去支农帮助生产队剥玉米。那年为了秋翻大会战,许多生产队的玉米都是连秆拉进场的。高高的玉米垛足有三四米高,每剥一穗要连秆从垛上拽下来,很不容易,剥的进度很慢。社员们根本干不完。玉米上大垛了,时间一长,粮食会变热发霉,需要学生抢救支援。再者,即使不天天支农,仅有的业余时间还忙着积肥呢!没有肥,再深翻也成不了卫星田啊!
第二学期,我们的卫星田种上了谷子,据说谷子根能深扎到凡是有肥的地方,能高产。卫星田是像菜地一样打的畦子,每株间距1.5到2寸。秋天到了,谷秆有香烟粗,大谷穗还真挺大,一穗能顶平常的三五穗。偶尔没有间开的地方,谷穗仍然很小,这决非缺水缺肥,而是阳光不足的缘故。
收获一算,亩产有千十来斤[ 当时的平均亩产为三四百斤。],我们“亩产万斤”的梦没实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可同学们付出的汗水,就是亩产万斤能划得上吗?
今天看来,我唯一的收获是认识到了中国人的耐力、潜力无穷。我们小小的小学生就能干出这种事,恐怕修长城的活儿我们也能干。
就是在那种苦干奋斗的环境里,同学们却总是乐哈哈的,有说有笑。因为当时当官的与大家一样,也没有私人利益。
想想今天,生活比过去好多了。社会风气却每况愈下,人心不齐,归根结底,恐怕是腐败风气所致,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担忧的事。
(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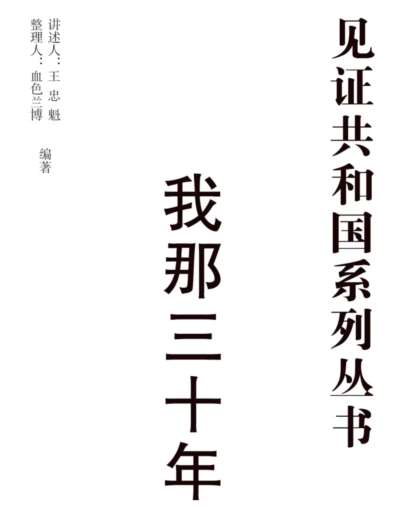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