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18下乡一

下乡与“扩大化”(一)[本章共22小节,分七次连载]
(1968年—1971年)
1.下乡插队的曲折
1968年8月初,正好是刚立秋忙着打柴的季节,我在家打了二十来天柴。在这期间,我抽空去公社革委会报到。但总是答复没有专人管下乡安置这件事,叫我在家等着。
一个月过去了,柴已经打够了,也拉进家里了。我第九次去公社问把我安置在哪个队,可还是没有消息。
我急了,对公社领导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指示上山下乡的,都拖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没合计好怎么安置我?”[ 这其实是用大帽子在压人,爸爸承认他更急的是不应该呆家中吃闲饭。家中九口人就靠爷爷一人工资养家糊口,既然不能升学了,就该立刻找个生产队挣工分来分担家庭的负担。]
几个公社领导碰了一下头又和我讲,他们一直没有接到旗里关于如何安置的消息,说:“你要着急就派你到蒙古艾勒[ 辽河从科尔沁沙地穿过,河两岸形成了黑土地,但更远处仍是沙地,河南边的沙地叫南坨子,河北边的沙地叫北坨子。蒙古艾勒是北坨子里的一个蒙古族聚落村。]当会计吧。”
我一口否决了。我说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能去当干部?蒙古艾勒缺会计是个老大难,那几年,每到年终,公社都要派几名各村较好的会计去集中整理几天账才能分红。我又不懂蒙古语,刚毕业就一个人当会计到那里,我不想这样“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非要当个名副其实的农民不可![ 主要原因是不愿离家太远好方便照顾家里。我问过爸爸,他承认了。]
之后,我几乎天天去公社追问。一直到我第十三次找公社,革委会主任才问我:“你个人意见打算落哪个队?”我回答:“当然离家就近安排好,西巴、南巴都可以。”领导们这才说:“那就西巴村吧,你照顾家也方便些。”我说:“行!晚上到大队部开会,学习离家近,我也方便。”
就这样,我跑了公社十三趟,直到9月20日,才解决了我在西巴村落户的问题。
发生这样的曲折,其实也不怪公社领导。在我刚刚毕业离校时,旗里还没组织集体户下乡,我安置后才有的保康镇先下乡。公社干部当时没有得到上边的通知,根本没有人负责“安置办”这件事。要不是我追得紧,我在家中再待上半年也不会有人过问我。我们是匆忙被“发配”毕业离校的,怎么“安置”是以后的事。那个年代,这种事不奇怪。
2.初试锋芒
从公社回来,我去了西巴大队[ 生产队解散后,原来的大队变更为村,公社变更为镇,西巴大队更名为西巴村。巴彦塔拉镇由四个村组成,分别是东巴村、西巴村、南巴村和北巴村。]二小队两个队长家,告诉他们我来插队落户的事。他们二人都很高兴我来他们队。这并不是因为我是高中生有文化,更主要的是,咱家就住在本队,全队的社员家都知道父亲的严厉是有名的,我平时在群众中的口碑就不错。
队里还没动镰,谢队长正在领一伙人帮盖房子的人家拓坯[ 坯是北方盖土房时用的原料,用和好的泥压在模具中制成约六块砖并排大小的矩形泥块,在太阳下晒干后使用。砖需要烧制但坯不用,它是用掺在其中的草来保证其坚固的。这活很累人,有俗话说:拓(读拖)坯打墙,累死阎王。]做帮工。他叫我等开镰秋收再正式上工。
我家也住在本队,和大家处好关系,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我说明天我也来帮工。
第二天三十来人在一块拓坯,我拿起二齿钩就和泥,干得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谢队长高兴极了,他说:“光听说你在家能干,想不到拓坯这农村的重活你也拿得起,一点看不出个学生样来!”
生产队第一天割地是9月25号,老队长邰文儒领男社员去割高粱。排垅时,邰队长慢慢地打了个高粱捆叫我看是怎么捆的,然后又割了一捆叫我试着打了个捆。我打过以后,他说:“行,就这样!”这是我接受“再教育”学农活的第一次割高粱,以前支农净割玉米、黄豆了,高粱谷子还没割过,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于是,二三十号人开始动了镰,队长打头是第一刀,我站在了第七位。虽然是刚学割高粱,可社员们谁也没有把我落下,都以为我干过这活儿呢。
割到了一百一二十捆,邰队长喊:“住刀啦!”我以为是半天活儿中的休息磨刀,可队长接着喊:“今天是头一天,先到这儿吧。有家什儿[ 东北方言,意指工具。]不应当的,回去好好收拾一下,下午接着干!”
下午割了二百多捆,中间歇了会儿大家磨了磨刀。
从第一天上趟子[ 上趟子就是许多人每人一条垅排成一条横队干活。由于人是有竞争意识的,每个人都不愿意被落下,所以上趟子是很累的。]干活儿,我就没挨拉[ 东北方言,落后的意思。]过,这要感谢我从小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从小磨练了自己的结果。而后来插队的知青,有的在队里干了一年,上趟子的活儿还跟不上社员,通过拓坯、割高粱的这几天小试锋芒,我心中有底了。这个当社员的活儿,我能干好!
后来三年的实践证明,队里的重活我挑得起,放得下,上手就行;许多农村的技术活儿,我学得也快。木匠干活,乐意找我打下手;跟车扶犁,老板子[ 东北方言,畜力车的车夫。]也愿意带着我。有些只有个别社员会干的农活儿,比如打海柙拍子[ 一种用柳条编成了席状器物,可以用于做房屋的顶棚或其它类似用途。]、打门帘、编筐织篓,我不但会干,而且干得比很多人都强。因此到了后来,反而是有些社员求我帮忙给他们干这些活了。这也是三年后选队长我得票最多,差点儿当上队长的原因之一。
尽管,对高中生下乡务农我是有想法的,总认为国家白培养了我们这么多年了,书本知识好像白学了。但是,当一天农民,我就要像模像样地做个农民,苦点累点对我不算啥。
3.我骂人了
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多被批成了“大毒草”,不能上映了。况且,镇里能来电影队也是偶尔的事。收音机,小舞台上也多是几部样板戏。实话说,虽然唱调不错,是江青亲自抓的文艺节目,如果她是在文艺界一直搞业务,不插手政治,名声也不一定会臭,也许会有个好下场,但总听就腻了,也不感到新鲜了。
生产队唯一的乐趣是干活时大家讲讲笑话,说说屁嗑儿,越是下流的越引人爱听,令人发笑,这成了农村活跃空气的一种独特的“文艺生活”。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也从不会口出脏话骂人。那个时代的学生生活使我养成了这种习惯,骂人也骂不出口。
可是,因为一件事,使我骂人了。
插队那年冬天,旗里公社下发了知识青年待遇:每人五十元钱,叫置办农具、家具的,还有十八尺布票、六斤棉票,还有二分木材证,共有五十个人的。
自从插队我整日同社员在一起劳动,而别人,持城镇户口的毕业生直到这时,多数人还在家中待着。别人知道消息得早,都领到了这份待遇。而我,几天后在场院打场时才听到了这个消息。
我到公社去领知青待遇,公社唐主任竟说发没了,没有我的份儿。我问他为什么,他支支吾吾地说:“你是先下乡的。”其实,是他把我忘了。我说:“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最先下的乡,公社最清楚。难道先下乡反而错了?”他回答说:“那名单上没有你。”
原来在我下乡一两个月后,后来初中的本镇毕业生陆续要求安排,公社才有了个大致的下乡名单,是发待遇前临时想的。
我说:“你公社的名单是怎么想出的?初中毕业生、农中学生,甚至小学毕业还有得到这份儿待遇的,他们都成了知识青年,我这个高三毕业的反而不是了?你讲讲,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知识青年?”
如果我问到此,他若能承认是公社因为我下乡最早,把我忘登记了,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可是,他以为他是公社主任,不想承认是自己的错,反而气急败坏地“解释”说:“别管你是什么毕业生,只要是全家吃红本的,年满十六岁的,小学没毕业也算知识青年[ 因为确实有小学没毕业领取的。],是文盲的也可以。”
听到这种混账话,我的肺几乎要气炸了,它深深地刺痛了我这个高中生下乡的心。我真想上去好好揍他一顿!可看他年纪比我父亲才小两岁,我忍住了。我骂他:“从我父亲和咱们多年相识的份上,我经常叫你大叔。可今天,凭你能说出这样的话,你真他妈的是个王八蛋!”
我接着大喊了起来:“我今天把话说到这儿:全公社如果只有一个指标,你都不能发给第二个人!我,不管你已经发完了还是没发完,你必须给我发!如果你不想重新发放,我揪着你明天就上旗里,叫旗里给我发!你有这个兔子胆儿去吗?!”
公社的其他领导,还有军宣队的队长,大家听到喊声,纷纷跑过来,询问为什么喊,老唐反而不吱声了。当他们知道了原由,劝解我先回去。我说:“唐主任没答应我,明天是不是旗里见,我不走。”军宣队长说了话:“小王,还是先回去。这事一定给你解决,你在家听信儿吧!”
第二天,通讯员就让我到公社领待遇。路上我问他是怎么解决的,他偷偷告诉我,唐主任不知从哪个发下的学生手中又抽回了一份,叫我去领的。
我并不是太看重了这点儿待遇,而是这件事太刺激我的心了。属实,公社只有一个指标,没有第二个人敢领,就应该是我的。就是旗里发放,我也是几个为数不多的,吃红本的,真正的老高三毕业生,更何况我又是全旗下乡最早的。如果只有一个指标,恐怕也应先给我发放。
知识青年待遇这事还使我联想到十八年以后的另一件事,那次还直接惊动了旗劳动局和教育局。
事情也和这次发待遇有关。1985年,工资调改,顺便有老知青补一事,并且,老知青的家属可以优先考虑农转非(变城镇户口)。可是,偏偏又没有我。
原来,1977年公社召开了一次全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大会,在会后给每人发了一份纪念品,有胶鞋、茶缸什么的几样东西,主要目的是慰问老知青。那时,我在校已经是教导主任了,工作正忙没有参加。事后同志们说你应该叫人去把东西领回来,我说算啦,我已经参加工作七八年了,有的至今还没有工作,旗里给的这点东西我不领了[ 为什么不领?应该得的要让,整理人是不理解的。],公社想给谁就给谁吧。
可就是这次到会的,公社列了张知青表送到了旗里备了案。当然,此时公社主任不是老唐了,统计的人根本也不会想到我还曾是知青。1985年的知青待遇恰恰就是以这张表为依据统计的。
涉及了知补,更涉及了家属和子女的农转非,使我不能不问一问,为什么又把我落下了。公社说明了情况,我没有怪公社,直接来到了旗劳动局。我讲了那年公社开会我没有去的原因,又讲了1968年发知青款的那一幕。我说:“名单上没有我不要紧,我毕业时的老师还都在,他们能证实我的情况。”
其实,劳动局也挺难的——调资办都撤了,如果改我的工资,全旗教育系统的工资统计表都要全改数字。
我说:“那你们看怎么办吧,要么找六八年的原始底案,要么我听听旗长们怎么处理。”
劳动局最后还是派人翻了翻档案,翻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那两页发黄了的纸张,字迹都不太清了的1968年知青待遇发放表。于是,他们又找了调资办的原班人马改工资表,之后单独为我列了一张调资表,叫我送到教育局备案,然后再改总数。费了好大周折,才解决了我的知补工资。
事情也怪,那年还有大学本科生家属及子女解决农转非一事,我的家属四口人农转非解决了。可不到一个月,公安局又来了一份同样是批准我家四口人的户口农转非,是照顾老知青的。这回我是老知青了!可这份户口我已经没有用了,只好作废留在了我家。一个月有两次农转非,也属于奇谈怪事了。
这件事使我想到,个人利益到底是争对还是让对?1968年我争知青待遇,争对了。1977年我让知青待遇,反而给后来的农转非、调资办、劳动局、教育局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1980年民主评议我让了一次给我涨工资的机会,又一次发扬了风格。同志们,特别是涨了工资的同志和领导对我很敬重,而我付出的代价是至今工资少了一级。当然,国家并没有亏待了我。
(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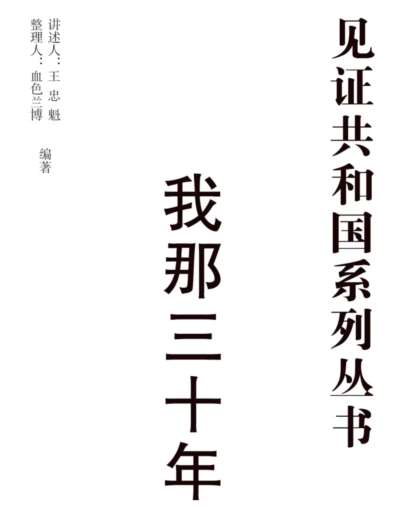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