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已飘起薄雪,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在寒风中愈发肃穆,而莫斯科大学礼堂内却涌动着滚烫的热浪。这一月,教员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开启第二次访苏之旅,从11月2日抵达时机场的热烈欢迎,到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参与12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密集议程,再到11月17日特意抽出时间与近四千名中国留苏学生会面,近二十天的行程里,每一个细节都镌刻着特殊的历史印记。尤其是在莫斯科大学礼堂里,教员那番饱含深情的讲话,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感慨,而是对旧中国青年血泪史的回望,对资本主义世界苦难现实的洞察,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坚守,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历史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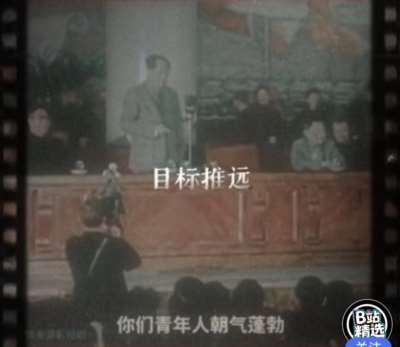
首先我们得回到旧中国青年那暗无天日的处境中去。1949年前的中国,青年们的青春从一开始就被钉在“牛马不如”的耻辱柱上。在上海的纺织厂里,十五六岁的青年女工每天要在轰鸣的机器前站立14个小时,手指被纱线磨得血肉模糊,稍有不慎就会被工头的皮鞭抽打。她们的工资微薄到连一顿饱饭都买不起,住在工厂附近低矮潮湿的棚户区里,冬天没有棉衣,夏天蚊虫肆虐,很多人不到二十岁就因劳累和疾病倒下。在北平的街头,无数青年学子怀揣着读书的梦想,却只能在垃圾堆里捡拾别人丢弃的书页,因为一所大学的学费就相当于普通家庭几年的生活费。即便有幸考入学堂,毕业后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绝境,1946年国民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高校毕业生失业率高达62%,许多青年只能沦为资本家的学徒,忍受着无休止的剥削和侮辱为“牛马”这种人格屈辱。
资本家们从不掩饰对底层青年的鄙夷与践踏。在天津的面粉厂里,老板常对青年工人说:“你们这些穷小子,生来就是拉磨的命,还想抬头做人?”他们把青年当作可以随意丢弃的工具,为了追求利润,故意压低工资、延长工时,甚至用童工替代成年工人。1948年上海《大公报》曾报道,一家火柴厂的青年女工因抗议工资过低被开除,老板竟放言:“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在这样的环境里,青年们的尊严被肆意践踏,梦想被彻底粉碎,他们就像被铁链锁住的奴隶,在黑暗中看不到一丝光亮。而那些出身稍好的青年,即便接受了教育,也难逃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在租界里,外国巡捕可以随意殴打中国青年,骂他们是“黄皮猪”;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进步青年稍有反抗就会被逮捕入狱,遭受酷刑折磨。1947年,北平某大学的一名青年学生因组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被特务秘密杀害,尸体被扔进了护城河,这样的惨剧在当时的中国每天都在上演。
帝国主义的铁蹄更是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划分租界,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在印度,英国殖民者的残酷掠夺导致1943年孟加拉饥荒,超过300万印度人饿死,而英国商人却趁机囤积粮食牟取暴利。在非洲,法国殖民者强迫当地青年修建铁路,无数人死于劳累和疾病,刚果河沿岸的白骨堆积如山。1950年代的越南,美国为了维护其殖民利益,悍然发动战争,炸弹摧毁了无数村庄,大量青年被迫逃离家园,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帝国主义的剥削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宣扬“种族优越论”,把殖民地人民视为“劣等民族”,肆意践踏他们的文化和尊严。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广大被压迫国家的青年们,都面临着和旧中国青年同样的命运,在苦难的深渊里苦苦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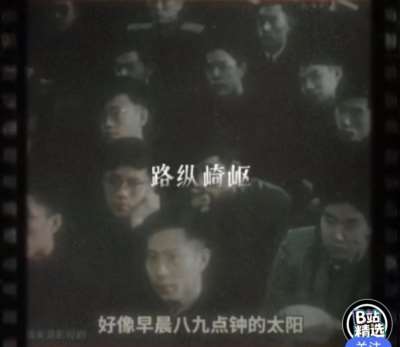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经过八年的建设,早已摆脱了旧中国的破败景象。“一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跃升至1957年的535万吨,为中国构建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框架。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青年终于挺直了腰杆,他们不再是资本家的奴隶,不再是帝国主义的附庸,而是国家的主人。那些留苏学生,大多来自普通工人和农民家庭,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全额奖学金,让他们能够在莫斯科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苏联的校园里,他们不用再忍受歧视和侮辱,可以和苏联同学平等交流,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一起憧憬未来的建设蓝图。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对比中,教员的讲话才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当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时,每一个留苏学生都能深刻体会到其中的深意。这不是一句空洞的祝福,而是对青年命运彻底改变的庄严宣告。在旧中国,青年们连生存都成问题,何谈拥有世界?而在新中国,青年们不仅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更有了参与国家建设、改变世界的机会。他们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生力军。毛泽东把他们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们身上那种摆脱苦难后焕发出的蓬勃生机,在莫斯科的实验室里,他们通宵达旦地钻研技术;在图书馆里,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在宿舍里,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回国后如何建设家乡。这种朝气,是旧中国青年从未有过的,是资本主义世界青年在失业和焦虑中难以寻觅的。
“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这番论断,更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苦难史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深刻认知之上。从旧中国被帝国主义肆意欺凌,到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赢得尊重;从资本主义世界深陷1957年经济危机,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失业率飙升,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科技不断突破。1957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下降13.5%,钢铁产量骤降50%,而中国工业总产值却增长18%。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两种制度较量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掠夺和压迫,它注定会遭到各国人民的反抗;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人民谋幸福,它必然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生动写照,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殖民统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股潮流势不可挡。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简单的一句话,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精神。这种“认真”,是与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敷衍塞责、贪腐无能相对立的,是无产阶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宝贵品质。在红军长征途中,战士们认真地保护每一份文件,认真地执行每一项命令,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绝不敷衍;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认真地发动群众,认真地开展游击战争,用“认真”的态度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在新中国建设中,共产党认真地制定“一五”计划,认真地建设每一个工业项目,认真地开展扫盲运动。这种“认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为了广大人民的幸福。它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担当,一种斗争精神。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认真地搞建设,打破了他们的经济制裁;面对旧中国遗留的贫困和落后,我们认真地发展教育和医疗,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种“认真”,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精神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
教员对留苏学生提出的“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青年的殷切期望。勇敢,是因为我们还要继续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还要克服建设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没有勇敢的精神,就会在困难面前退缩;谦虚,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不能因为取得了一点成就就骄傲自满,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需要不断吸收先进经验。“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是对青年全面发展的要求,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投身革命斗争;只有掌握扎实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建设国家。而“和苏联朋友亲密团结”,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形成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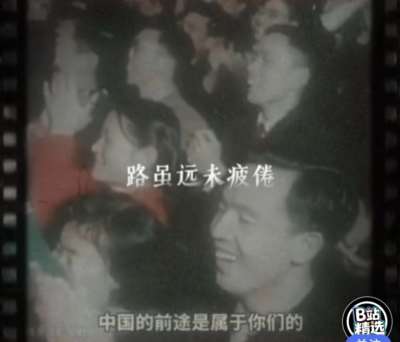
当时的留苏学生们,正是带着这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精神,在苏联刻苦学习。他们中,有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王永志,当时25岁的他在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把“认真”二字刻在心里,在学习中一丝不苟,回国后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有投身钢铁工业的专家,他们认真地研究每一个炼钢工艺,为新中国的钢铁产量突破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从事农业研究的学者,他们认真地培育每一个粮食品种,努力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些留苏学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无产阶级革命青年的“认真”,能够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力量。
回望1957年莫斯科大学的那番讲话,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青年的期望,更是对旧中国苦难历史的告别,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反抗,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精神的坚守。旧中国青年的牛马处境,帝国主义带来的深重苦难,都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逐渐成为历史。而教员所倡导的“认真”精神,所寄托的青年希望,却穿越时空,依然激励着我们。在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种“认真”的革命斗争精神,依然需要青年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朝气蓬勃地投身到国家建设中去。因为我们知道,不管在资本家、官僚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看来,你我这些年轻人是多么不值一提,在教员看来我们是未来的希望,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还在继续,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只有保持“认真”的态度,只有依靠青年的力量,我们才能在新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才能让“东风压倒西风”的历史潮流继续向前推进。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