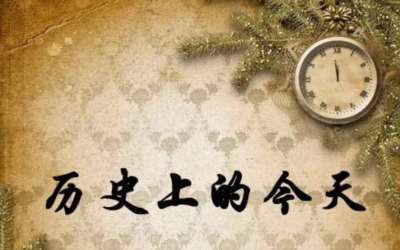
深秋的北京已然透着寒意,但四九年十一月初的这几天,这座城市的气氛却比天气更加凝重。市场上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信号正在积累,粮价在悄然攀升,棉纱的价格波动幅度越来越大,就连街头小贩手中的零星商品,标价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战役即将拉开帷幕,这场战役的核心,本质上是价值规律在新旧生产关系交替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与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集中爆发。任何商品的价格波动,本质上都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而价值规律本身又始终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独立存在,在那个旧秩序崩塌、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过渡时期,这种依存关系展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一种极度失衡的状态,多年战争的摧残让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濒临崩溃,生产力的严重受损成为价值规律失常的根本前提。工业领域的景象最为惨淡,1949年的生铁产量仅剩下25万吨,还不到历史最高年产量的四分之一,钢产量更是跌至15.8万吨,只有历史峰值的17%。作为工业的基础能源,煤炭产量仅有3200万吨,较历史最高水平下降了近一半,发电量也减少了28.3%。民生工业同样遭受重创,棉纱产量下降24.5%,棉布下降32.3%,就连糖和卷烟这样的日用品,产量也分别减少了一半以上。农业方面,耕地荒芜、水利失修,粮食产量远未恢复到战前水平,许多地区甚至面临着饥馑的威胁。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价格的波动理应围绕着价值这个轴心上下摆动。但在1949年的中国,生产力的全面衰退已经彻底打乱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基础,钢铁厂无法正常开工,纺织机大量闲置,农田产出不足,商品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就失去了稳定的参照标准,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也就必然出现严重扭曲。这种扭曲不仅是个别行业的现象,同时其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环节的系统性紊乱,它使得价格不再是商品价值的真实反映,反而成为投机资本操纵市场的工具。
生产力的严重不足直接导致了商品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这为价值规律的扭曲提供了现实土壤。按照价值规律的基本作用机制,当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涨会刺激生产者扩大生产,增加供给,进而使价格回归价值中枢。但在1949年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自发的调节机制完全失效了。当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状态,官僚资本刚刚被没收,国营经济还在初创阶段,私人资本在工商业领域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流通领域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私人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供给短缺的背景下被无限放大,他们非但没有因为价格上涨而扩大生产,反而纷纷选择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在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投机者们集中抢购银元、大米和棉纱,通过控制流通环节人为加剧供给紧张,导致价格在短期内疯狂飙升。1949年6月,上海的银元价格从每块兑换100元人民币,短短两天就涨到1100元,带动市场恐慌情绪蔓延。银元风潮平息后,投机资本又转向粮食和纱布,7月上海每石大米价格从1万1700元飙升至6万5000元,一个月内物价上涨一倍,这种涨势很快波及北平、天津等地,两地物价一个月内上涨三倍以上。到了10月,棉纱价格再次成为投机焦点,一个月内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进而带动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4.9%。这种现象看似是违背了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实则恰恰是价值规律在私有制占主导的生产关系下的一种必然表现。因为当生产资料掌握在追求短期暴利的私人手中时,他就一定成为资本逻辑的代言人。这就导致价值规律刺激生产、平衡供求的积极作用被抑制,而通过价格波动实现资本增殖的消极作用则被无限放大。
货币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其自身价值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价值规律的正常运行,而1949年的货币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货币的价值本质上由发行方的信用和社会生产能力共同支撑,二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当时的货币流通领域存在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旧政权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尚未根除,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早已沦为废纸,人们对纸币的信任度降到了冰点,民间更愿意以物易物或使用银元进行交易;另一方面,新政权发行的人民币刚刚开始在全国流通,尚未建立起足够的信用基础。1948年12月1日,人民币在石家庄正式发行,起初仅在华北、华东、西北三区流通,直到1949年9月才被确立为全国法定本位币。由于解放战争仍在进行,财政支出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支撑,导致人民币发行量迅速增加,而与之对应的商品供给却严重不足,这使得货币价值缺乏坚实的物质依托。以上华北地区批发物价为例,以1948年12月为基数100,到1949年3月就涨到261,5月更是飙升至380。货币贬值与物价上涨形成了恶性循环,物价上涨迫使政府增加货币发行以维持开支,而货币供给增加又进一步加剧物价上涨,使得人民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职能逐渐失效。这种状况不仅破坏了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更使得价值规律失去了有效的表现载体。因为此时的货币本身的锚定的价值都在剧烈波动,商品价格自然无法准确反映其内在价值,整个经济体系陷入了严重的价值混乱。

要扭转这种价值混乱的局面,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显然行不通,必须建立起能够驾驭价值规律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而统一财政政策的提出,正是构建这种基础的第一步。财政政策的统一性绝非单纯的制度设计,它必须建立在相应的物质基础之上,否则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这个物质基础的核心,在于国家对关键经济资源和重要物资的掌控能力,尤其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棉花、煤炭等“两白一黑”物资的集中控制。而这种掌控能力的获得,首先源于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到1949年解放前夕,官僚资本已经垄断了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控制了钢产量的90%、电力的67%、有色金属和石油的100%,以及几乎全部的金融机构和铁路、航空等关键基础设施。新政权通过接管这些官僚资本企业,迅速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国营企业在现代工业中的比重达到了50%左右,其中发电机容量占73%,钢占90%,水泥占60%。这种对核心生产资料的掌控,使得国家具备了生产和调配重要物资的基本能力。在此基础上,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物资调运,从老解放区调运棉花,从北方调运煤炭,从四川和华东周边调运大米,集中力量充实战略物资储备。尽管这个过程充满困难,有些解放区因自身粮食短缺而不愿调出,从四川运米到上海的运费甚至与收购价相当,跨区域调运还面临着交通破坏的阻碍,但通过统一协调,大量关键物资还是被集中到了中央手中,为稳定物价准备了物质前提。
这种物质基础的构建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生产关系变革中重新确立价值尺度的过程,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为强力行政力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条件。在正常的商品经济中,价值尺度是通过无数次的商品交换自发形成的,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自动调节资源配置。但在1949年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私人资本的投机行为和区域壁垒的存在,使得自发的价值尺度形成机制完全失灵,价格信号彻底失真。要重新确立合理的价值尺度,就必须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打破私人资本对流通领域的垄断,建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收官僚资本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革命。将原本属于封建买办阶级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所有,消除了最腐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这就为新的经济秩序建立创造了条件。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直接催生了强力的行政力,这种行政力并非简单的强制手段,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基础上的组织协调能力。国家通过建立统一的财经管理机构,将分散在各解放区的财政收入、物资调度和货币发行权集中起来,打破了区域分割的局面。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第一次将所有解放区的财经负责人聚集在一起,商讨统一的物资调拨和财政政策,标志着这种行政力开始形成。会议明确提出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发行库、统一税目税率、建立国营粮食和纱布公司等措施,从制度上保障了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掌控。这种行政力的本质,是新的生产关系在国家治理层面的体现,它使得国家能够超越局部利益,从全局出发调配资源,为驾驭价值规律提供了组织保障。
行政力的强化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扫清了障碍,而货币政策的落地又进一步巩固了价值尺度的稳定性,二者形成了相互支撑的辩证统一关系。当时货币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人民币获得市场信任,使其真正承担起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这就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控制货币流通总量,二是为货币价值提供坚实的物资担保。行政力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通过统一全国现金管理,要求所有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必要开支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实现了对社会资金流动的有效管控,从源头上抑制了货币滥发的冲动。更重要的是,行政力保障了物资储备与货币发行的匹配,当10月物价再次疯狂上涨时,国家能够动用行政系统的组织能力,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物资。到11月25日前,各地按照统一部署,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集中到重要城市,形成了强大的物资储备力量。25日当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大量抛售储备物资,投机资本原本以为物资短缺会持续加剧,纷纷高价囤积,却没想到国家有如此充足的货源,在持续的抛售面前,价格一泻千里,投机者纷纷亏本破产,再也无力操纵市场。这场较量的实质,是行政力保障下的物资供给,战胜了私人资本操纵的虚假需求,使价格重新回归到与商品价值相匹配的水平。货币政策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关键在于行政力确保了货币发行有足够的物资支撑,人民币的价值通过国家掌握的粮食、纱布等商品得到了证实,从而逐步建立起市场信任。
这场稳定物价的斗争,说明了经济规律的作用形式总是与特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而革命的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对经济基础具有强大的能动反作用。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向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的特殊矛盾决定了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必然带有过渡性特征。一方面,商品经济依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价值规律仍然在商品交换领域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价格涨跌依然是调节供求关系的重要信号;另一方面,旧的生产关系正在被摧毁,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这使得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成为可能。革命的政治生态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是要通过外在于经济的强制力量解决问题,而是要调动这个经济内部中生产关系变革的自觉因素,瓦解旧世界政治生态的基础。这种政治生态本身也深刻认识到,生产力的恢复离不开稳定的经济秩序,而稳定的经济秩序又必须建立在对价值规律的科学把握之上。因此,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通过统一财经集中物资,通过强化行政力实施调控,这些革命政治生态的实践工作,本质上都是为了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为价值规律发挥积极作用创造条件。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内在统一,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政治生态反映着经济基础,并通过自身的变革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而经济基础的发展又会推动政治生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完善。
由于战争破坏了交通线路,加上各地存在的贸易壁垒,1949年的中国市场呈现出严重的分割状态,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差异巨大。这种区域间商品流通的不畅,演变成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另一大障碍,而行政力推动下的统一市场建设,则为价值规律在更大范围内的正常运行创造了条件。比如,常州不让粮食运到上海,赣东北对杭州实行粮食禁运,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纷纷设立流通壁垒,这种区域分割使得商品无法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自由流动,加剧了局部地区的供求失衡。当时的革命者通过行政力,用两个方面的行动打破了这种分割,一是全力恢复交通运输,修复铁路、公路和航运线路,为物资流通扫清物理障碍;二是通过统一的物资调拨政策,强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要求各解放区服从全国统一安排。当时从东北调运数千万斤粮食支援上海,从四川征集4亿斤大米进入华东市场,这些调运行动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依靠了行政力对地方资源的统筹协调。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使得商品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地区间的价格差异逐渐缩小,价值规律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发挥调节作用,商品价格也开始更准确地反映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标志着价值尺度的进一步稳定。
生产能力恢复与价值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稳定物价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而这种关系的实现,同样离不开革命的政治生态在全国领域的变革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商品价值量的基础,只有当工业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品供给能够满足社会需求时,价值稳定才能获得坚实的物质支撑;反过来,价值的相对稳定又为生产力恢复创造了必要条件,当物价稳定、货币信用建立后,企业才能准确核算成本和利润,生产者才有扩大生产的动力和信心。稳定物价的胜利为这种辩证关系的展开创造了前提,而革命的政治生态在实践中则在其中扮演了统筹协调的角色。国家通过国营企业组织工业生产恢复,修复被破坏的工厂设备,组织工人返岗复工,同时在农业领域通过减租减息等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50年,随着生产的逐步恢复和财政收支的平衡,全国物价开始趋于稳定,工业生产也逐渐回升。这种发展不是自发实现的,而是革命政治生态行动下的自觉过程。通过把握生产与流通的辩证关系,将恢复生产与稳定物价作为同等重要的任务,既通过物资调控稳定价值尺度,又通过价值稳定促进生产发展,体现了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用。
1949年的稳定物价事件不仅解决了当时的紧迫问题,更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但其作用形式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这场斗争的胜利证明,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价值规律发挥积极作用时,通过革命手段变革生产关系,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经济秩序,就能使规律的积极作用得到释放。行政力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其建立在全国人民自愿且自觉地组织起生产关系变革的基础之上,这符合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趋势;货币政策之所以能够落地,关键在于它有坚实的物资生产和流通作为支撑,这遵循了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相统一的规律。革命的政治生态则为这一切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它使得人们能够超越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从历史发展的全局出发制定策略,这正是人类社会实践区别于自然过程的自觉能动性所在。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价值规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复杂表现,也能深刻体会到生产关系、行政力、货币政策与价值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1949年的中国,正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物质基础,依靠物质基础构建行政力,以行政力保障货币政策实施,最终使价值规律回归正常运行轨道。这个过程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在认识其客观性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内部条件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革命的政治生态作为贯穿其中的内核,始终围绕着解放生产力、建立稳定经济秩序的目标,展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这种将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将生产关系变革与经济运行调控相统一的实践,为理解历史发展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也为把握经济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