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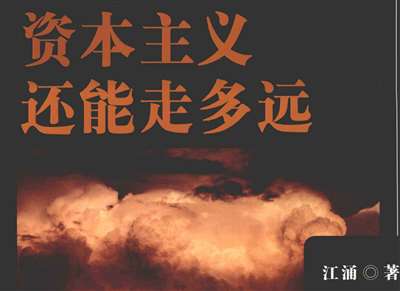
连载2
绪论
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还是“动荡与危机”?
次贷危机、债务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银行危机、货币危机等系列金融危机,正加速国际力量失衡、格局变迁、秩序调整,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然步入金融动荡、经济低迷、社会对立、政治僵化时代。西方主导的时代走向终结。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崛起,发达国家的衰落与新兴市场的崛起,既广且深地改变着国际格局,冲击着国际秩序。改变现状与维持现状抑或革新与守旧的力量之间的误判、对峙、冲突或将难以避免,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国际社会稳定的基础日趋脆弱与薄弱,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而且进一步滑向“战争与革命”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如此给那些“利用和平,实现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
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
近三十多年来,与金融发展和深化进程相伴的,越来越多的不是相关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而是金融动荡与经济迟滞。伴随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与扩张,国际金融动荡日趋常态化。
基础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经济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经济空心化,虚热实冷情形严重,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国民经济呈现明显的“倒金字塔”结构,头重脚轻。在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贡献却在40%以上。次贷危机爆发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是实体经济的6-8倍。国际每天外汇交易中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交易只有1%多一点。这种头重脚轻的怪状必然不利于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的稳定。二是国际收支严重失衡。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在产业空心化、国民经济虚拟化后,不断利用储备货币与国际分工优势,吸收世界商品、服务,成为净进口国,导致国际收支失衡日益严重,集中体现中美国际收支失衡、跨太平洋国际收支失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三是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当今世界前15大债务国,全是发达国家,占据世界信用资源的90%。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财富创造、消费品制造的主力,但是能够利用的信用资源十分有限。而发达国家耗用世界绝大多数资源不是用来生产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用来消费,甚至战争等消极开支。
结构性裂变。一是金融资产结构发生裂变,欧美诸多银行“有毒资产”远远超过自有资产,甚或超过正常资产。2009年2月,欧盟委员会报告披露,欧盟银行体系的“有毒资产”数额高达25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欧盟GDP(13.6万亿美元)的183%。此后,希腊等欧洲主权债务风险急剧增加,原本被“巴塞尔协议”认定为“零风险”主权债券,如今与美国次贷一般成为“有毒资产”。随着欧债危机不断恶化,“有毒”规模将日趋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认为,根据以前发生的120次银行危机的经验,不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经济复苏。二是金融市场结构发生裂变,资本市场超过货币市场,市场投机远远超过市场投资。当今世界原本有两大类金融模式,即以美英为代表的直接融资模式,和以德日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模式。上世纪80年代后,美英模式盛行,而后近乎一统天下。国际融资由此便由资本市场占据主导。但是,由于金融创新过滥,金融监管缺失,金融异化严重,资本市场上投机力量逐渐占据主导,金融大鳄横行霸道。对众多投机者尤其是金融大鳄而言,厌恶市场稳定犹如细菌厌恶真空一般,因为只有动荡,才有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有报道显示,2011年夏金融大鳄索罗斯利用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进行市场做空,就赚取10亿美元。
连锁性危机。2008年在基础性失衡、结构性裂变情势下,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引爆次贷危机。危机爆发后,美英等国以无限量发钞、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暂时平息了危机。但是,引爆危机的根本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政治家们的裱糊下焖烧得更加严重。“私人债务国家化”使本已居高不下的西方政府债务问题进一步恶化,那些处于金融链条最薄弱环节、同时又是经济强大国家危机转嫁对象的弱小国家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基础性失衡、结构性裂变更加严重,如此国际金融市场风声鹤唳,稍有风吹草动就大起大落,动荡连着动荡,而且日趋频繁、日益加剧。在希腊债务危机之后,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等都极有可能成为“多米诺骨牌”。在标准普尔推倒“不倒翁”美国AAA主权信用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进入了三大评级机构的负面观察名单,全球经济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安全港湾”,过去的“稳定之锚”现如今很可能成为“动荡之源”,国际金融市场将由此遭受一波接一波的冲击。因此,综观当今国际金融,债务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等金融危机都在排队酝酿,无论哪一个率先爆发或集体爆发都不奇怪。西方大国与国际经济组织已近乎弹尽粮绝,救不胜救。
极限性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乌云压城的态势下,美欧等经济大国纷纷以邻为壑,拼命以量化宽松、货币贬值等方式转嫁危机。三大评级机构明显在落井下石,时而不时抛出降低某一经济主体等级的震撼弹。对冲基金等金融秃鹫密集市场布局,做空相关经济主体。如此,相关评级机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等组成的“金融联合舰队”(抑或“金融猎杀队”)不断火中取栗,有意无意将信息——能量——物质“三态”的转换发挥到极致,实现相关强权国家政治利益与机构商业利益的极大化。正是因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等连锁性危机冲击下,国际投资者犹如惊弓之鸟。在一波接一波的金融“大洪水”面前,银行紧缩信贷,企业紧捂荷包,消费者为明日不测而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在连锁性危机冲击下,政府越来越难以构筑金融防波堤,市场越来越难以找到经济止损线,投资者、消费者信心丧失殆尽,一些深陷危险漩涡的重债国家政府倍感挫折,自救已经无能为力。在连锁性危机冲击下,金融、经济动荡加剧社会、政治动荡,而社会与政治动荡反过来也会加剧金融与经济动荡,相互激荡,金融动荡成为常态,金融稳定遥遥无期。
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
国际金融加剧动荡且动荡呈现常态化,加速资本主义组织机制的裂变与衰变,资本主义生产力在连锁性金融危机下遭遇连环破坏,发达国家经济引擎普遍放慢乃至失速,处于实质依附状态的新兴市场自主增长力量严重不足,如此世界经济失去了常规动力,疲态尽显,极有可能呈现出“倒根号形”()——危机衰退后的长期低迷。
资本主义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资本主义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在经典作家那里有过清晰表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的巨大生产力集中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的一种自组织机制,不断激发技术创新、集聚劳动者技能以及催生企业家精神,并把这些积极要素在企业法人这一组织架构中进行有效整合,以最小化成本为社会提供产品与服务,谋取利润最大化。如此,使资本主义保持很好的财富创造效率。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美式自由资本主义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世界经济由此实现新一轮繁荣。然而,随着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的发展,技术创新、劳动者技能、企业家精神均不断衰弱,资本主义的微观经济基础遭到空前削弱,资本主义自组织机制愈发僵化,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削弱。连锁性金融危机连环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可预期的将来,很难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顺利修复。
发达国家经济引擎普遍放慢。除了生产力不断削弱这一趋势性因素外,还有重要的周期性因素,即周期性生产(包括金融产品)过剩与消费萎缩带来的制约与冲击,集中表现在金融危机在欧美国家持续焖烧与延烧,严重冲击破坏实体经济,损害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所倡导的去杠杆化、再实体化、经济外向化,收效甚微,远不足以扭转经济疲弱态势。尽管奉行莱茵模式资本主义国家(集中于斯堪的纳维亚及德国),依然有着较好的增长与发展势头,但是这类经济体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比重较低,非但难以引领西方、进而引领世界走出困境,反而又可能被欧洲其它重债危机国拖入泥潭。奉行英美自由经济模式的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占主导地位,他们的经济状况不仅决定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而且广泛而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有鉴于此,一段时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界鼓吹的所谓“大稳健”神话彻底告破。
新兴市场自主增长力量不足。近年来,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不仅自身实现了强劲增长,而且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作出重要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的增量多半来自新兴市场,而且贡献的份额正越来越大。但是,新兴市场近乎都奉行外向型经济,以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愈发倚重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实质经济依附。但是,如今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正遭遇金融危机与经济低迷的困扰,银行放贷谨慎,企业投资减少,消费者消费能力与意愿降低,如此对新兴市场的商品与服务需求,以及直接投资都呈现出不断萎缩态势。此外,新兴市场没有自己的储备货币、没有自己的金融服务系统、没有自己的定价机制,这些领域近乎完全依赖主要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金融动荡以及风险转移、危机转嫁不可避免地殃及新兴市场。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新兴市场投资与消费过热,国际热钱肆虐,资产泡沫严重,通货膨胀居高难下。未来,无论是国际游资还是直接投资,都有可能从新兴市场急速大规模撤离。果真如此,一些问题丛生、管理不力的新兴市场很可能遭遇新的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国际金融大鳄获取暴利、美欧转移风险与转嫁危机所期待的。
发达国家社会矛盾尖锐化
2011年春,突尼斯发生骚乱,很快在相同质地的北非中东形成火烧连营之势,这就是所谓“阿拉伯之春”。就在西方列强煽风点火、火中取栗之际,“欧洲之夏”、“美国之秋”不期而至,在雅典、罗马、马德里、巴黎、伦敦等欧洲城市集会、游行、罢工乃至骚乱间歇,波澜壮阔的“占领华尔街”行动却在资本主义的心脏、策动他国反政府运动的大本营中掀起。此起彼伏、声势日渐浩大的群众运动,正令西方社会日渐陷入动荡的漩涡之中。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将资本主义的特征经典般概括为“创造性毁灭”。长期以来,在自由经济的催化下,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成果”为少数人独享,“毁灭的代价”由多数人承担。当世界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候,“毁灭的代价”由殖民地、半殖民地承担。二战后的几十年间,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承担着“毁灭的代价”。如今,在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的“双刃剑”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不断觉悟,尤其是新兴市场实现群体性崛起,拒绝承担“毁灭的代价”。如此,越来越多的“毁灭的代价”不得不由发达国家的大众承担。在美国,最富有的1‰(约30万)的收入与最穷的50%(约1.5亿)的总收入相当,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70%。诸多发达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英国、法国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如此,直接激化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
在美国,“婴儿潮”一代,一个白领家庭,一个男人一人工作,就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过上很体面的生活,实现美国不断宣扬的“美国梦”。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后,近30年间普通劳动者实际工资没有增加,与管理者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大约从40:1飙升到357:1,中产阶层“上流化”基本停滞,“下流化”日趋严重,中产阶层坍塌导致社会由“橄榄型”蜕变为“M状”,贫富日益对立。在生活的重压下,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走上了工作岗位,尽管如此,夫妇两人工作支撑的家庭很多也只能勉强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适逢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越来越多的家庭只有过紧日子、苦日子。年轻一族的尊严损伤更是严重,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在8%到10%之间,而年轻人的失业率在20%左右,有色人种的年轻人更是严重。
在西方国家,美国的情形总体处于马马虎虎的中上水平,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奉行莱茵模式的国家日子较好外,其他国家情形只有比美国更加糟糕。西班牙平均失业率在20%左右,不满25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甚至超过40%。这些精力旺盛、不名一文的年轻“无产者”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基本力量,是“愤怒者”、“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力。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诱导下,美欧等国纷纷出手,用纳税人的钱财,救助贪婪无良的机构,激化了矛盾。当政府将私人债务国家化后,主权债务风险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由此被推向危机的边缘。为减少财政赤字,阻止债务进一步攀升,相关国家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开支——主要是削减福利开支,由此进一步侵夺了中产以下阶层的利益。
金融动荡、经济低迷无疑恶化了中产以下阶层的生活境况,激化了年轻人对政治与社会的不满,如此,社会矛盾日趋汇集,星星之火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要改变现状,争取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而欧洲蔓延于希腊、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的抗议,则是要维护现状,捍卫现有的社会福利。西方国家金融动荡、经济低迷,不仅构成本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基础,也成为国际金融、经济、社会与政治动荡的源头。
西方民主政治普遍僵化、弱化
金融、经济危机成为检验所有政党、政府、政治精英强度韧性的试金石。实践表明,西方民主政治普遍僵化、弱化,政坛充斥的是眼中只有党派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政客,政治家、战略家成为绝对的稀缺品,如此不仅无法有效应对危机,而且还放大、恶化危机。西方多年来所鼓吹的“民主”,非但不是什么“先进”、“普世”的好东西,而是问题本身,是西方政治僵化、弱化的肇始,是各类危机孕育、恶化的源头。
自由与民主本质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资本主张一元一票(如股东),而不是一人一票(如工会),而民主的本质是伸张大众的权力,要求就是一人一票。在资本主导社会的前提下,一人一票永远敌不过一元一票,如此在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地位不断下降。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越来越不可得兼,要真正给予大众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利益集团的经济自由。正因如此,资本扩张、经济全球化显然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失业率居高不下,工薪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降低,中产以下人群的生活日趋窘迫。
正是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与矛盾,资本主义下的民主政治,只有热闹的形式,而实质都集中到自由经济,各类大资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要雨得雨,要风得风。正是大众不满徒有虚表的民主形式,如此对投票选举的热情不断递减,对政党、政客的不满与日俱增,不仅有激烈的言辞,而且更有激烈的行动,因此西方政权的合法性正面临危机。在美国,社会的左倾化与政治、经济精英的右倾化形成鲜明对照,民粹主义已经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跑了出来,如茶党的活跃,政治极端化倾向愈发严重。
民主政治使政府被利益集团左右的倾向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如此政府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应对危机、突发事件的能力,越来越低。政治民主原本是穆迪、标普与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赋予AAA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标普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了美国国债的偿还风险。多年来,将“民主”作为“普世价值”而到处兜售的美国,在危机面前更是灰头土脸,围绕国债提限、财政减赤,共和民主两党恶斗,人为导演了一场危机,令本国大众失望,让国际社会嘲笑,重创了“世界领袖”的声誉。世界普遍质疑:一个金融上成为国际动荡源头、经济入不敷出、社会矛盾尖锐、政治愈发无能、思想日趋保守、动辄以邻为壑的美国,如何引领国际。由此显示,全球化下,危机关头,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而越来越成为制造或恶化问题的源头,成为问题的本身。
世界见证了民主的“日本速度”——六年换了七任首相,犹如世界经济中曾经出现的“拉美化现象”,国际政治如今诞生了“日本化现象”。日本政治俨然成为国际政治家、政治学者嘲弄、揶揄的对象。当下,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危机,因为欧洲一体化起因、进展无一不是政治积极推动的,但是民主政治一方面使得欧盟成员国在国内受大众民主、民族主义牵制,另一方面欧盟集体运行机制上受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掣肘,如此在危机面前无效、低能,坐困愁城。落入危机漩涡的欧盟边缘国——“欧猪五国”政府逐一更替,核心国政治也岌岌可危。
西方民主政治僵化、弱化不仅对西方国家政府应对各类危机提出严峻挑战,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协同应对危机、加强国际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在新兴市场尚未赢得经济话语权、政治主导权的情势下,国际社会如何适应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是一个严峻而严肃的话题。
西方不断延烧的金融危机使凯恩斯主义走到了尽头——财政刺激政策形成公共债务悬河,更令新自由主义走到了尽头——利率、流动性等陷阱使各类常规货币政策无效。与此同时,西方又没有勇气搞社会主义。因此,美国为首、西方主导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无主义”也就是没有发展方向的危险境地。次贷危机使投资者与机构之间失去基本信任,金融危机救助使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金融风险转移与危机转嫁使国家之间失去了基本信任,“无信任”令经济保护、贸易摩擦日趋严重,商品服务无法正常交易,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国家之间也难以有效合作。资本主义失去了重心与中心,G7心力交瘁,G20力量涣散,金砖国家有力无处使,世界正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秩序”阶段。在“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情势下,国际巨轮业已驶入一个陌生水域,可怕的是无动力,无舵手,亦无航海图。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尖锐化,西方民主政治普遍僵化与弱化,如此全球各类乱象将长期持续。“阿拉伯之春”、“欧洲之夏”、“美国之秋”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失速正给全球带来的“经济寒冬”,这表明:“动荡与危机”或将取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而“战争与革命”一不留神很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选项。毕竟,在世界人类历史上,“动荡与危机”甚或“战争与革命”似乎比“和平与发展”更显常态。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