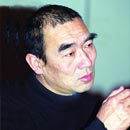《北庄的雪》
A.Maemura(前村)
古巴的烈日,像一个残酷的暗示。
我在火烫如银的暴晒中走向他,眼角凝着一层盐末。那真不像参观,而是一个仪礼。我抬起十八岁就迈开的腿走向他,好像这是最后一步。
先是望见一尊高耸白花花毒阳中的雕像,接着就看见了他。我写过一次,说出了当时的感受:那是抚弄亲人的遗体、与他肌肤擦碰的感觉。亲人的遗体隐喻的,是一种残酷的亲近。
他是一个深刻的话题。死了半个世纪,但依然惟他才是主角。他安详而英俊,让人莫名地联想耶稣。我的周围伫立着默哀的人,他们互不相识,各个来自世界一隅,他们专程来悼念他,哪怕对革命有所保留。
那天我垂目凝神,没有发现纪念馆墙上的浮雕——
都是他的游击战士,他们在墙上凝视着我们,平和而静默。
一个日本电影《埃内斯托》(Ernesto),描写了一位日本裔玻利维亚人马埃木拉(Maemura、前村),他是格瓦拉队伍里的战士,在游击队的化名和格瓦拉的名字一样:埃内斯托。而且他就牺牲在那场著名的、玻利维亚山谷里的战斗。
同胞里有过一名格瓦拉战士这件事使左翼日本人不能忘怀,因此一定有人会把它拍成电影。电影新星小田切让居然全程使用西班牙语,令人对这一代日本影星刮目相看。
小田切塑造了一位天性平和、诚挚待人的医学院学生,他的天性是善良和正义,所以扛起枪也合情合理。他的履历像一切学生那样平凡,他的牺牲也像一切士兵那样突兀。
在恐怖的胁迫下,农民出卖了游击队。激流跋涉中,埋伏的枪响了。格瓦拉游击队里著名的战士,华金、塔尼娅,都倒在中流,血染红了河水。化名“埃内斯托·医生”的他受伤后被俘。
若不是他喊出了自己的名字马埃木拉(Maemura、前村),或许人们永远不知道游击队曾有过一位日裔战士。
但使我心头颤栗的是另一个细节:
杀死他的政府军士兵,居然是他幼时的伙伴!……这使一切像被黑漆刷过,一切都晦暗了。
值得提及一下这个“当兵的”,他的名字叫迪托。这是一个赤贫家庭的儿子,性格阴郁自卑。而前村家开着一个杂货店,经济比迪托好得多。
家境好些的马埃木拉喜欢帮助人,常给迪托家送药和吃的。电影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但是没有对迪托多加刻画。在那一瞬,当马埃木拉大声喊道“我是Maemura”时,也许他渴望过一线生机?
可是,认出了前村的那个士兵却对昔日的朋友举起了枪。一边恶狠狠地说:“我认识他!总穿着好衣服好鞋……”
在最深的潜底,隔阂与妒恨每一刻都在悄悄发酵。阴暗的血,在冰冷地无声流淌。原来行善未必有感恩的回报,所以一旦黑夜阴森地巡视,“恶”便窜游着挑唆。魔鬼在那一刻活跃着,谁也不知暗霪中发生的变化。
阴沉的士兵在电影中没有露出面部。霪雨湿冷,一个黑影端枪站在雨幕里,如一个暧昧隐形的魇影,扑灭了残存的希望。
所有的抗争,都在那一笔浓稠黑色之前放弃了。濡湿丛林里孤独的死,撕开了历史的脸孔,那么肮脏,那么无情。民众的儿子被民众杀死,他血肉淋漓地躺在祭坛上,向我们讲述“牺牲”的含义。
牺牲是一个秘默的话题。它是人类最古老、最阴暗的习俗。将亲生儿子献祭的故事是古代残酷的遗痕,每个接受了它的民族都会重复悲剧;每个被它纠缠的人,都难逃一种宿命的厄运。
难道是为了向这一种阴影宣战么?——欧美的青年一连几代,并不加入诅咒的合唱。他们不喜欢梦魇,异端之美让他们着迷。
于是对格瓦拉的怀念经久不息。面对滔滔雄辩的诅咒,“青年不理睬它”。这不也是一种真实么,格瓦拉依然矗立,而诅咒者并未取胜。
是的,民众的愚昧与隔阂,并不能抵消对光明的投奔。这样的投身不能被轻易忘怀。所以在电影里,文质彬彬的医学院学生和肩抗步枪的战士一体和谐。埃内斯托·前村被枪弹击中了,鲜血流入丛林的泥泞。在栽倒在暗夜的泥潭之前,他突然回过头来,隔着雨帘,望了我们一眼。

日本电影《埃内斯托》镜头截屏
B.Kamui
对于在酒店研讨会上阔论革命、离底层实践躲得远远的“左派”精英,不存在这样的命题。哪怕他们拥挤呱噪,但只显示了知识分子的堕落。虽然那些泥泞血迹与民众纠缠一体的志士确实在远远一隅,愈来愈形只影单了。
这是一个少数人的话题。
我见识也窄,只知道日本漫画家白土三平借“木间党”的故事深入过这个题目,当然是在巨著《カムイ伝》(卡姆依传)里。
几十年我摆脱不开这么一个念头:白土三平究竟是在替他的父亲一代(岡本唐贵,日本早期普罗画家同盟领袖),还是为他自己(日本的六十年代左翼学生称《卡姆依传》是阶级斗争教科书)开掘到如此的深层呢?或者,既然拥有了这种体验,他要对阶级与革命进行总结?
(1)
《卡姆依传》描画了一个武士出身的少年草加龙之进。当民众被无休止地蹂躏压榨、在饥饿离散的苦难中挣扎的同时,龙之进的武士之家也在上层政治中崩溃,草加一族遭到恶意构陷,被全家灭门。武士少年龙之进也沦为最底层的“非人”,从而刻骨地体验了什么是身份歧视。
再生的他身心蜕变一新。他的选择是“革命”,匡正世道。
故事的高潮是他组织的游击队,名为“木の間黨”。他们不是忍者,亦非剑侠,而是有严密纪律(掟)的军事集团,翦恶救弱,神出鬼没。飞将军常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受苦与施暴的现场。他们把从奸商处夺来的金钱抛撒给穷人,美少年剑士蒙面遮眼,一骑马一把刀,如黑暗底层射进的炫目亮光。一个鼓舞人的、希望的局面出现了。
但统治者设计了恶毒的诡计:派一支假木之间党潜入乡间,模仿木之间的方式,喊着木之间的口号,捣碎门扉,屠戮山村,烧杀淫掠,行凶作恶后再打着木之间党的旗子扬长而去。
污名化的毒辣手段一旦奏效,先锋与底层之间的盟誓和信任,就莫名地开始龟裂变质。同志被离间了。
百姓只认眼前。穷、贫、清贫、赤贫——这些类似的中文词汇,含义远不尽同。人若是一旦从孩提年幼就堕入了赤贫绝境,他的骨头若是一旦从幼年就被强酸腐蚀,那么他的人格难生硬质。
经历了极度的饥肠与卑微之后,多数人会一生膜拜金钱、权势、物质。这也是解释一切出身底层的贪官污吏的依据。
假作真时真亦假,“底层民众”被煽动起来了。
在人民的咄咄敌视下,先锋陷入孤立。木之间运动遭到了意外的惨败。霉运常是双重的:一度从武士贵族跌坠到非人部落,由于尝遍了阶级的苦辣才投身斗争、立志颠覆阶级制度的龙之进——更遭到了“谋求回归武士阶层的战友”的离弃。
拷打折磨只属于他个人,没有谁伸出援手。局势急转直下,暗黑的历史又添了一笔绝望。
历史黯然掀过了这一页,所谓革命的一页。
(2)
坚决反对武力匡世、主张体制内合法斗争的,是另一个主人公正助。
他助人为乐,勤恳聪明,不在乎僻远寒村的农夫千般苦。他日出而作,逆来顺受,梦想着耕有田食有米的前景。在大饥馑袭来濒临绝灭时,他挺身农民先头,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一揆”。
在中国解释这个日本史的“一揆”很劳神。一揆是造反,也是恭顺;是冒犯的下克上,也是下对上的表忠。是疯狂的打砸毁(打ち壊し),猛打猛冲但冲到“上”的阶下,却奴隶般地齐齐跪下。
面对这种咆哮一时的底层,领主阶级善作虚伪的让步。但让步附有条件:首谋者要承担秋后算账,一般都被酷刑之后枭首。

加沙2025
农民领袖正助被捕后,为了不使他死后成为农民崇拜的宗教式英雄,官府阴险地把他放生,以便农民们认定他是叛徒。但又先割掉了他的舌头,让他有口难辨。
惨剧发生了:浑身血迹的百姓忿忿于自己的付出,迁怒于活着回来的正助。他们不能容忍逃离了祭坛的牺牲,咒骂正助是出卖的叛徒。
须知在几十卷长篇叙述之末这样的画面是无法接受的,但底层的穷困愈真实,它制造的悲惨就更真实——褴褛血污的百姓抡起镰锄一拥而上,围住自己敬爱的领头人,将他残忍地活活打死。
换言之:实行武装斗争的革命者,执着于合法斗争的改良者,都在统治者的强力与欺骗之下被瓦解了。
奋斗失败,志士惨死,黑色的描绘撕裂了心。思想还可能突围么?

长旅之一(1980)
评论家总结说,这部作品描述了——“前卫怎样在民众的孤立下走向自灭,而民众在反动派的宣传下怎样被非理性地煽动”。
一点都没错。但我好奇的是:作家从哪儿获得了类近的体验。
因为我不相信缺乏“类近体验”能够达到理解——这是我坚持的文艺批评理论。有过体验的人虽少,但会在似曾相识的岔口出现。他们会觉得如同阅读自己,并从中感到共鸣。
这个过程——类近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度及不同的历史中,像一个循环在独立地运行。有时会洞彻与理解,让良知一瞬跃进;也有时会惜身缄口,最终皈依资本的宣传。它们在秘密梭巡,思想与魔魇攀缠角斗。
这是思想的奥深,并非任人都有资格插嘴。
只有实践的人,只有那些真地投身、甚至作过“牺牲山羊”的一部分人,才能撕开伤疤,露出赤裸的脉动。
——我仿佛突然惊醒,那个电影使我受了过度的刺激。
日本人只想纪念他们之中有过一个格瓦拉战士,而我却如作了一个噩梦。我暗自在心里驱散它,甚至暗暗捧起双掌,祈求“从魔鬼的侵扰中”护佑自己的安宁。但我更明白:它不是魔鬼,它是社会的真相。它是一个暗黑之魇,虽然并不常见。

长旅之一(1970)
C.底层
哦,底层。环绕周围的尽是小利忘命的智识阶级,哪怕这个词汇被他们挂在口头。他们是辛勤的泥瓦小工,在利益的小楼上添砖加瓦。
而另一极,命定底层的人却在缄默,在角落里撕碎了稿纸。
何况如今,底层是最难定义的。你读这一篇时可能已是西历2084年,比起著名的《一九八四》预言已是百年之后。反正离那一天——马大学在“文明与对话兰州双年展国际综合论坛”发表《论远寺妥协的合理与合法》论文、李万金取得了美国西海岸十家出版社的代理权——又隔了不止半个世纪。
马大学的原名叫马上学,后来他偷偷自己改名“大学”。而且偷偷跑寺里,要求阿訇把经名字改为“北大”。因为他听人说,北大念着像经上的balda(城市),马马虎虎是“圣人坐的地方”。他讲演那天,说是美以英法的大使都来了,就坐在他“底层”老爹的旁边。
至于李万金,原是种洋芋的好手。没“南巡”他就把洋芋贩到了啥都吃的鸭子广东。但他几辈子最羡慕读书人,拿卖洋芋的钱做本改行书商,口号是“让书比洋芋更多”。再以后时来运转,如今他是国际出版界的巨头,转卖版权,炒作热门,俨然已执牛耳,令知识界老九们对之折腰。
巧的是,他俩的父亲都是我的熟人。
儿子一边长大,一边却与我一寸寸隔阂。他们的眼球游移不定,总闪烁着一丝似是亲近、更是怀疑的神色——如托尔斯泰写的:“目光都流露出一个问题”。
我知道那问题是什么。和那个穷当兵的迪托一样:您“穿着好衣服好鞋”,知道种洋芋多苦么?
我从没打算回答,我只等着他们选择。
当资本得心应手地煽动,民众呼啸而起扑杀自己的先锋——那时知识与文学究竟还能有什么作为,是个新的题目。我想着,凝视着它。

长旅之一(1984)
D.“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托翁式的命题。
托尔斯泰不为上述的事发愁。他相信一种独特的待人方式:“经过两三次对视以后”,彼此就不再互相害怕,而且接受的“双方都是人”。
他也不惧怕自己的单纯。他敢用一口学生腔直率地问妓女“您靠什么吃饭、您靠什么过日子”?
招来嘲笑之后他照样睁大眼睛说:“不应该责备她们,而应该同情她们。难道是她们的错?”
就是要这样,读着托翁的传记我浮想联翩。以你的坦荡,对付一切复杂。
实际上,托尔斯泰以他的真挚,以他对光明的信仰,解开了知识分子的大难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是一部与底层结合的指南。
靠他冥冥的教示,我在自己的天地里也照样行事。本来是“同伴在关口前会怎么样”,摸索中成了“我们该怎么过这一关”。
一旦念头变了,明亮的光就照了进来。投身正义是气质的选择,是一类人的生存方式——不在意世俗的结局,却在结局战胜了世俗。
啊,对光明的笃信和跋涉……这样话题便变移为信仰。

在喀喇沁旗用蒙文题词
并非只有少数不知顺从潮流的人,并非只有被厩食的奴隶放肆地嘎嘎大笑着嘲笑的失败者——从血肉的真人到艺术的形象,前村、龙之介、托翁,都在这条路上。
历史的危机正聚合大势,或许顷刻一霎,滴水就会变为洪流。
漠然望着左右流过的人群,俯瞰着人与人磨踵擦肩,但直直地彼此两界。但我想,人群里依然确有真挚的伙伴。想到这儿的一瞬,我突然意识到一道目光——视野里埃内斯托·前村正转过身,凝视着我。
光明的吸引不可抗拒。
我不禁迎着他走去。脚迈开了,我怕他会倏忽消失,别的抛在脑后,我只想追上他。
2021年4月26日写成,
9月青海天课归来改于飞机上
收入散文集《心之愉悦》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